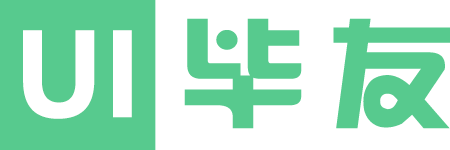(王玉虎 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副主编)
推荐语:
从历史上看,一段高速发展的经济繁荣,总是伴随着文化思想的改弦更张。美国20世纪早中期,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以及科技发明的重大突破,给社会和文化带来重磅冲击。经济自由空前高涨,使得束缚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财务枷锁放松了很多,思想和文化领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彼时,知识阶层的崛起,冲刷着整个社会观念,颠覆了人们的普遍价值标准。围绕这场运动的核心价值观是“自我、自由和自主”。以当时欧洲的价值观看来,发生在彼岸美国的这场静悄悄的价值观改变无疑是“粗鄙的”。不过,最终是美国改变了世界。
稍事比较,彼时知识界的活跃和大胆,要比今天活跃在中国的“公知”走得更远、更彻底。概因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结构,对知识界的束缚要少得多,而旧观念反倒成为主要束缚。回到今天的世界来看,知识阶层对旧观念的突围,可能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使命。

知识分子的反抗
文/Frederick Lewis Allen?译/译科 孟洁冰
对德战争结束的时候,社会力量的强制性成了遍及全国的习惯。一个思想守旧的美国人对少数人的权利没有多少热情。他在开拓传统的熏陶下长大,习惯于使用现有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比如说道德规范法令、治安委员会,必要时也会动用霰弹枪。历史书里的《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固然写得不错,可等到他自己处理事情时,通常抱有这样的想法:自由不过是许可的代名词,《权利法案》是对待流氓恶棍万不得已的手段。在战争期间,美国人发现,通过宣传进行立法,逼迫邻居接受自己看来顺理成章的行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宣布和平后,他还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让他们继续言听计从。
美国人把精力从自由债券运动——每个人都要购买一定数额的债券,稍有怠慢就会受到威胁——转向各种活动,如社区公益金活动、大学捐款基金活动、教会成员活动、推动城镇建设活动,还有其他数不胜数的公共活动。各家委员会及其分会纷纷成立,新闻广告员大量派发新闻,演说家大声疾呼。要是有人紧紧捂住自己的钱包,就会感到忐忑不安,承受公众舆论的压力。正如我们亲眼所见,过去对敌国侨民和亲德分子的高压统治,与后来对激进分子和布尔什维克的残酷镇压只有一步之遥。战争时代的审查制度,与和平时代对报纸书籍和公共演讲的审查制度只有一步之遥。战争时代的禁酒法,与战后永远写入宪法的禁酒法,以及载入法典的公众道德规范也只有一步之遥。当然,曾经在1917年和1918年饱受束缚的商界,已经挣脱了大多数的桎梏,因为当今的普通美国人把切身利益等同于商业利益。不过在商界以外,他自以为深知人们应该如何行事,对胡言乱语一律不予理睬。
红色恐怖时代的初期过后,美国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激进主义,对商业坚持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这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而工人们不是遭到警察的威胁恐吓,就是受到拥有股权的诱惑,希望自己变成有钱人。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在几年前还准备献出生命,冲破最低工资法案、平等选举权和集体谈判权的障碍,如今却感到痛苦绝望,灰心丧气。他们毅然断定:政治不过是一幕粗俗下流的闹剧,世上的糊涂虫总要比文明人还多,这些蠢货被选区里吞云吐雾的政党领袖牢牢握在手心里,投票权简直就是笑话。福利事业同样是白费力气,统统乏味无聊、感情用事、狂妄自负。在1915年,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年轻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为了参加社会主义的游行,不惜断绝父子关系;到了1925年,他们却把社会主义叫做老古董,对此不以为然,完全不在乎钢铁公司员工的报酬是高还是低。社会风尚已经发生了如此变化:如今,思想反叛的年轻人会反对一夫一妻的制度,亵渎上帝,把自己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
然而,当大多数中产阶级从迫害政治激进分子转而约束个人行为时,他们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其中不仅有年轻聪明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新生群体,这就是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美国信使》杂志称为“少数的文明人”,开始大声疾呼,奋起反抗。
这些严阵以待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组织有序的群体。知识分子的思想大相径庭,即使大家意见一致,作为个人主义者,他们对建立组织的想法也会深感厌恶。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纽约是他们的主要据点,不过在很多城市的中心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知识分子中主要包括艺术家、作家、职业人士、大学城里思想不安分的学者,受过大学教育的商人阶层里,能够看懂比《星期六晚邮报》和《麦考尔杂志》更复杂的文学作品的人。
在这段反抗的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的信条究竟是什么?以下就是一份简略的概要,但是没有几个人会全盘接受。不过,也许可以表明他们总体意见的大致倾向。
第一,他们信奉性自由观念,认为这方面应该比严格的美国道德准则所允许的范围更开放。从战后开始,他们就沉醉于菲兹杰拉德小说里年轻思想家的缠绵悱恻,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的大胆宣言兴奋不已,因为米莱声称自己心力交瘁,无法度过漫漫长夜。他们还对同性恋文学作品兴致勃勃,有数千人前去观看尤金·奥尼尔那部长达5个小时的精神病理学戏剧《奇妙的插曲》。他们阅读的文章、谈论的话题、心里的想法全都与性有关,对那些表示反对的人不屑一顾。
第二,他们尤其蔑视通过立法来推行礼仪规范,对由此产生的影响深恶痛绝。他们厌恶卫理公会派的游说者约翰·S·萨姆纳和所有支持审查制度的人。他们把清教徒,甚至是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都描绘成面孔铁青、嗓音粗哑的伪君子。在他们眼里,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既下流龌龊又滑稽可笑。在他们看来,萨克雷、丁尼生、朗费罗以及19世纪波士顿文人的声誉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他们坚信,短裙和文学戏谑的时代开启了新的启蒙运动,年轻的知识分子嘲笑《生活》杂志里描绘的19世纪90年代的“欢乐时光”,和托马斯·比尔一起,屈尊行贵地把“紫红色十年”的蓬松衣裙和闪烁其词的小说打量一番。实际上,有些知识分子似乎认为,除了古希腊文明时代、卡萨诺瓦时期的意大利、交际花风行时期的法兰西和18世纪的英格兰,现代社会以前的所有历史时期都显得荒谬可笑。
第三,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禁酒运动强烈反对,对审查制度深恶痛绝,对政治重建和社会复兴抱有疑虑,进而怀疑所有的改革运动,不信任所有的改革家。他们绝对不认同自己是同胞兄弟的守护者;一个人不把宽容看作至高无上的美德,就让他们无法容忍。如果有人在进步思想家的晚宴上,听到有人说“法律制度太多了”,应该让人民自由生活,那么他就会在100场宴会上听到这句话。在1915年,改革家通常被当作赞扬的词汇,而在1925年,这个词——起码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成了带有轻蔑意味的称呼。
第四,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宗教怀疑论者。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大声疾呼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要少于19世纪90年代,一方面是因为怀疑宗教不再被看作耸人听闻的想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对宗教的知识分子认为,福音派教会没有急切地按照他们的形象改造别人,于是他们感到心满意足,平静地走出了教堂。人们不禁怀疑,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美国大学生,是否会像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一样,在讨论普遍取消大学礼拜仪式的时候,平心静气地说,“聪明人是不会再信仰上帝了”。不断思考的公众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书籍,而这些书从一开始就认定他们的读者抛弃了古老的宗教体系。
第五,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大多数中产阶级不屑一顾,因为这些人正是禁酒运动、审查制度、原教旨主义和其他压制行为的根源。他们纷纷效仿门肯,厌恶巴比特式的庸人、扶轮社会员、三K党成员、微笑服务、拉拉队和超级推销员。居住在城市中心的知识分子深感自豪,自以为比愚昧偏远城镇的居民地位优越,正是这些地方造就了巴比特式的庸人。比如说,1925年《纽约客》创办的时候,杂志的箴言就是“不是给迪比克的老太太看的”。他们格外看不起那些成群结队涌入欧洲的美国游客,倘若有人坐在甲板躺椅上,而他旁边的乘客在膝盖上放了一本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新小说,他就免不了要听一番议论,说法国某些地方别致优雅的小餐馆,还没有“被美国人给糟蹋了”。
第六,他们尤其以颠覆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偶像为乐。威廉姆·E·伍德沃德在1923年出版的小说里发明了“揭穿真面目”这个词,成了知识分子流行的做法。林顿·斯特雷奇写的《维多利亚女王传》成了1922年美国的畅销书,随后有一大批暴露真相的传记纷纷出版。鲁珀特·休斯剥去了乔治·华盛顿的华丽外衣,引发了一场骚乱,因为他在演讲中宣称:“华盛顿是牌术高明的专家,酿造威士忌的行家,赌咒骂人的高手,他和手下得力干将的太太跳上三个钟头的舞都停不下脚步。”传记作家纷纷描写其他美国名流的错误缺点,把史上臭名昭著的坏蛋挖掘出来,塑造成形象生动、魅力非凡的人物。结果有一段时间,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一位传记作家想获得成功,就得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
第七,他们担心大量生产和机械化对自己和美国文化产生影响,在这个福特主义和连锁店式思想高度垄断的国家,他们把自己看作争取文明权利的最后防线。他们痛恨受到严格管制,这种情绪推动了思想进步的学校运动,产生了高等教育的创新举措,如安提阿、罗林斯和米克尔约翰在威斯康星州建立实验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其他大学的荣誉计划。这种情绪同样推动了小剧院运动,使之在全国各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学校里。当代小说的主人公都被刻画成这种形象:家乡的气氛让他感到窒息,为了逃避这种精神状态,他来到了曼哈顿,最后来到蒙帕纳斯或里维埃拉。
在巴黎任何一家咖啡馆里,你都能找到一个美国浪子,庆幸自己运气不错,终于摆脱了标准化的生活,却忘记了这个事实:遍布路边咖啡馆的法国与充斥着汽车和收音机的美国一样中规中矩。知识分子欣然接受外国演说家对美国文化的批评,而这种批评的数量简直多得史无前例,优秀杂志上刊登着以“我们美国的蠢事”和“幼稚的美国人”为题的文章,月复一月在他们眼前出现,他们却没有耿耿于怀。他们期望听到这样的说法:美国渐渐沦落到野蛮状态,对于文明人而言,这是个根本不能生活的地方。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哀叹道:“我在考虑一个实际的个人问题,那就是一个略有资产的普通人,生活简单,乐趣单纯,而且习惯思考,怎么样能在本国找到一个地方,如何生活下去。”
我要提醒一句,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里,很少有人会接受以上所有的信条。但如果有人一条也不相信,那他就不是开明人士,不能算是真正的文明人,也不能算是现代人。繁荣的花车隆隆向前,而站在路旁的知识分子吵吵嚷嚷,露出一丝嘲笑和失望。
节选自《仅仅是昨天》
法律出版社2011年2月
感谢本文推荐人:王玉虎 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副主编,欢迎更多朋友推荐美文,小编代您与大家分享。
(毕友推荐——分享MBA推荐的文字。毕友推荐,旨在收集和整理MBA推荐的各类原创或转载的文章和资料,每日定期发布,分享给所有的朋友。通过每个人的推荐分享,实现大家单位阅读时间价值最大化。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请将您的推荐直接发至邮箱:2696039404@qq.com或Q:2696039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