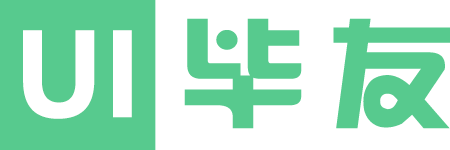有段时间,我和太太很喜欢打台球,我们两个人都打得不好,但是在台球厅一边打着球一边聊天,在这个城市里,是件比在空气污染的街道上散步更好的饭后运动。
就是在有一次这样的无意间,我们聊到父亲,妻子问:“为什么你爸爸去深圳那么早,却没有做得很好?我看你爸爸的老同事都还不错的。”
在我的父亲退休时,是一个机械公司的研究所的所长,是个非常专业细致的机械高工,在深圳退休工资不算高,不如在民企做经理的妈妈。
我告诉他,在我初中升高中的一年,爸爸有一个机会,升做发展部主任。当年很多在内地无法运作的项目,都在深圳特区进行。发展部则是谈商务合作的部门,毫无疑问是个肥差。爸爸走马上任。做了半年,发现有两大不适应,第一是平时总是需要出差,第二是在家的时候应酬多。很多人过来拜访送礼。我小时候是人来疯,一有人来,我就不好好做作业。而那一年我初三了。
作为孩子,我不知道爸爸是义无反顾还是轻轻松松做了这个对他事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就和公司提出换岗,成为了公司的研究所所长。从此他不再出差,那个学期的晚上,我们家关上大灯,不开电视,拉上窗帘,躲开所有希望来坐一会的同事。我在客厅借着应急灯的灯光看书,而他们则在阳台小声聊天,偶尔过来摸摸我的头和背,送来一碗水果。那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太太有点奇怪的打断:“有人来,你爸爸可以让你在房间里面学习啊,而且那个时候你又不要你爸辅导功课,他完全没有必要在家——其实我觉得这个牺牲对你考上高中没有什么用。”
我瞄准一个绿球,呼出一口气,推出一杆,说:“你这么一说,好像的确没什么用。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家庭的每个人都更加信任对方。年龄越大,我就越了解父亲的牺牲有多大。我们就越知道对方能为这个家付出些什么,这让我们家庭这么多年,虽然有很多冲突,但是一直很幸福。”
她点点头,没说什么,我们继续打了下去。
一直到晚上临睡的时候,她才突然说:“我想起自己家里的很多事,我突然明白,原来我的家里,缺的就是这么些没用的付出。”
说完这句话,她哭了。
高度在很多时候可以转化为宽度,温度,效果却不会马上显现,信任会作为账户,在很多年以后储存起来,酿成美酒。
而一件事情有用没用,也许只有时间与生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