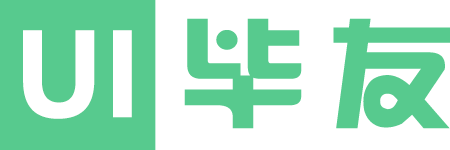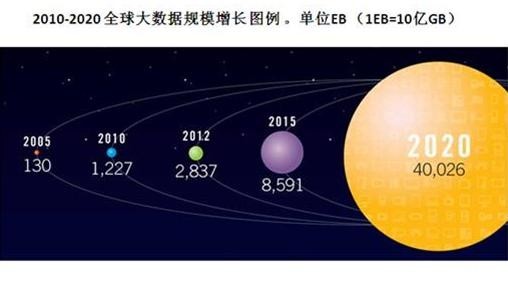(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李淼 )
推荐语:
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吗?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和做出如何行动的决定是听命于我们自己,还是事先被设定好的?这是在西方宗教和哲学中存在了两千年并被不断争论了两千年的终极问题之一,到了二十世纪末,这个问题也进入了科学领域。也许,在不远的未来,科学将对这个问题做出终极裁判。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与人类大脑如何工作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会驱动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认知科学以及意识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稍稍思考了自由意志问题之后都会被带入天人交战的处境,天自然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条件,包括整个宇宙的历史,宇宙大爆炸,我们的父母将我们生下来,这个社会在我们发育和受教育的过程中给我们提供的帮助以及没有给我们提供的便利,而人是我们自己。
对大脑研究的最新进展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和做出如何行动的决定不完全是显意识在主导,潜意识、左半脑和右半脑的协作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也许是更重要的作用。问题归结为,到底什么是“我”?肯定不仅仅是显意识。关于自由意志或自主的争论,有时往往停留在显意识的层面,这明显是不对的。比如做梦,如果将显意识排除,出现的不是“我”而是自动机?我想多数人肯定不会同意,所以,“我”是大脑的整体协作的结果 。
毫无疑问,先天遗传的基因以及后天的神经发育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都会对我们施加影响,这些影响有时导致犯罪。在作出如何处置一个罪犯的决定的时候,这些因素应该被考虑进去。但是,不能仅仅因为这些因素我们就可以完全忽略“我”的自我动因,否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理由去犯罪而不受到处罚,处罚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环境”,它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先给惩罚一个理由
译/欧阳明亮? 文/Sam Harris
正是因为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我们才会接受宗教上的“罪恶”观念,并坚决支持“报复性”的司法正义。任何危及自由意志存在理由的研究进展,似乎都会让人怀疑惩恶罚罪的道德合理性。
当然,最让人们担心的是,如果实事求是地强调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可能会全面消解人类的道德责任。如果人类的行为完全受制于像天气般变化无常的神经活动,我们如何能准确地讨论善恶对错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保留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念中找到与我们发现的客观事实相符的一面。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人们平常所说的“对某个行为负责”究竟是什么意思?举例而言,昨天我去逛了一趟超市,当时我穿戴整齐、举止检点,没有做小偷小摸的事情,也没有买凤尾鱼罐头。这些行为与我自身的想法、意愿、信仰或者欲望完全一致,二者之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关系。
正是从这一点上说,我完全可以对这些行为负责。但如果我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超市里,而且企图一罐又一罐地偷走超市里的凤尾鱼,那么我的行为举止就完全是一种反常的表现。我会认为自己肯定是中了邪,并觉得自己不该为这些行为负责。因此,责任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我们头脑的整体状态,而非超脱于物质之上的精神层面的因果关系。
化解仇恨的理由
我们不妨看一看下面五个有关枪击事件的案例:
1.某男孩,4岁,他在玩弄父亲的枪时杀死了一位年轻女子。这把枪原本放在梳妆台的抽屉中,枪里面装满了子弹,并且保险栓是打开的。
2.某男孩,12岁,经常遭受肉体与精神上的虐待。某天,他用父亲的枪故意杀死了一位嘲弄自己的年轻女子。
3.某青年,25岁,小时候饱受虐待。他故意枪杀了自己的女友,因为这个女人移情别恋,离他而去。
4.某青年,25岁,幼年时家庭环境非常良好,从来没有受过虐待。他故意枪杀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5.某青年,25岁,幼年时家庭环境非常良好,从来没有受过虐待。他故意枪杀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只是觉得好玩而已。”然而核磁共振显示,在他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控制情绪和冲动行为的区域)长有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
在以上任何一个案例中,都有一位年轻女子死于非命,而且她的死亡都源自另一个人的大脑活动,但我们对此会产生多大的义愤,却取决于每个案例所涉及的背景条件。我们认为,一个4岁大的孩子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杀人意图,而一个12岁的孩子在思虑的周密性上还无法达到成人的深度。
因此在案例1和案例2中,我们知道杀人者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因此他们都属于不完全刑事责任人。
在案例3中,长期的受虐经历以及突如其来的感情纠葛似乎可以减轻这个男人的罪行:这是一次激情犯罪,杀人者本身也受到过别人的伤害。
在案例4中并不存在虐待的问题,根据其中的杀人动机,我们可以将这位杀人者认定为心理变态。
案例5所涉及的变态心理和杀人动机与案例4完全一样,但杀人者脑部的肿瘤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道德判定:鉴于肿瘤生长的特殊部位,这位杀人犯几乎完全不用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尽管他的主观意图与案例4中的变态杀手如出一辙,但他却能出人意料地规避道义上的责任,因为一旦我们了解到他的主观情绪源自某种生理原因,即脑部肿瘤,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自身生理缺陷的牺牲品。
可见,在以上所有案例中,造成这位年轻女子死亡的真正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另一个人的大脑状态及其相关的背景因素,但其中涉及的道德责任却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别。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
为了证明某些人具有社会危害性,我们往往会接受这样一个假象:每个人都是自身想法的施因者。然而,我们完全不必如此。当一个人对他人造成伤害时,他的行为是否出于明确的意图,是我们谴责他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依然可以根据具体案例中的相关事实来进行量刑:例如,被告的品性特征、犯罪记录、人际关系、酗酒经历,以及所供认的犯罪动机等。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已经完全失去理智,我们就应该充分考虑他的存在将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如果被告冥顽不化,嗜血如故,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他对社会存在危害,而无需借助自由意志的观念。
为什么蓄意伤害他人的决定最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依据明确计划而实施的行为最能反映出我们大脑的整体特征,诸如我们的信仰、欲望、目标以及偏见等。打个比方,你产生了刺杀国王的意图,你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并且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还和自己的朋友发生了争论,最后你依然决定刺杀国王,那么你的刺杀行为充分说明了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并不是说你的行为根源于你自己的决定,完全受你自己支配。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原因如何,你偏偏长了一个弑君者的大脑。
为了防止他人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将某些罪犯投入监狱。这样做的道德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其他人会因此受益。抛弃自由意志的假象可以让我们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例如评估风险,保障无辜以及制止犯罪等。然而,当我们将更为广泛的因果关系纳入考量范围的时候,我们的道德直觉就会变得更加宽容。从确切的意义上说,即使最凶残的暴徒也是因为人生的不幸而沦为罪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仇恨(而非恐惧)的理由就会土崩瓦解。即使你相信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如果某人生来就拥有一个心理变态者的灵魂,那么他显然是一个极度不幸的人。
为什么案例5中的脑部肿瘤会完全改变我们对事实责任的认定?原因之一是,如果没有遭受脑部肿瘤的侵害,当事人(根据我们的假设)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肿瘤的生长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算作一种偶然因素,由此而言,杀人者完全是自身生理缺陷的牺牲品。当然,如果他的病情无法好转,我们仍有必要将他囚禁起来,以防他再次实施犯罪,但我们不会仇视他,或者将他视为邪恶的化身。我相信,我们的道德直觉必然会朝着这个方向改变:我们对人类大脑背后的因果关系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难在案例4与案例5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治疗罪恶的药剂
那些被关在死牢里的男女囚犯只不过是一系列不幸的集合体:不良的基因、糟糕的父母、恶劣的环境、愚蠢的想法。他们显然都是些倒霉透顶的无辜者。在人生的这些变量中,有哪一个是他们可以真正负责的对象?已经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一个人的生理基因和成长环境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但是,没有人能够对自己的基因或成长环境负责。我们的司法体系应该体现这样一种认识:在人生的牌局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抓到一手烂牌。事实上,道德本身就掺杂着运气的成分,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有违我们的道德原则。
我们的道德直觉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现在发明了一种可以治愈人类罪恶的方法,结果将会怎样?假如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成本低廉、安全无痛的手段让大脑活动产生相应的改变,譬如说,我们可以将某种药物直接添加到食品当中,就如同添加维生素D一样,那么所谓的“罪恶”就只不过是一种类似营养不良的疾病。
假如这种治疗罪恶的方法真的存在,我们就能明白,人们的复仇心理存在着道德上的缺陷。也许到了那一天,我们可以拒绝给一个杀人凶手提供相应的治疗,作为对他所犯罪行的一种惩罚。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这意味着有些人理所应当地被排除在治疗范围之外?如果在一个人实施犯罪之前,我们原本有机会将他治好,那他是否仍然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似乎那些对他的病情早有了解的人更应该因为疏忽大意而受到起诉。对于案例5中的凶手,我们已经知道脑部肿瘤是他犯罪的真实原因,我们也可以为了惩罚他而拒绝对他实施手术,但这是否说得过去?显然说不过去。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惩罚的念头,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
尽管人们钟情于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大多数人都已明白,即使是最美好的想法意图,也敌不过大脑疾病的负面影响。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说明我们对普遍人性的看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更深刻,更合理,也更具怜悯之心。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认识的发展显然与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背道而驰。根据宗教教义,每个人生来就拥有一个永恒的灵魂,这个灵魂完全不受物质世界的任何影响,包括这个人的生理基因或者他所身处的经济体系。然而,这种观念其实最容易为人类的暴行提供生存空间。
将人类行为视作一种自然现象并不会破坏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如果能将地震或飓风关押起来,以阻止它们施虐,我们同样应该为它们建造监狱。我们不遗余力地抗击传染病毒,甚或杀死一些偶然出现的野兽,但我们从不认为它们也具有自由意志。很显然,即使将有关人类行为根源的真相大白天下,我们依然可以明智地应对社会危险分子所造成的威胁。我们仍旧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统,根据犯罪分子对社会构成的潜在威胁,它可以准确地进行定罪量刑。但是,惩罚的理由则会自行消失——除非我们发现惩罚是达到威慑或恢复目的的必要手段。
复仇的欲望是一种错觉
必须承认,有关复仇的问题总是让我们感到左右为难。美国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在《纽约客》杂志发表过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文章讲述的是如果一个人复仇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他有可能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戴蒙德对比了两个人的真实经历。
一个是他的朋友丹尼尔,这位新几内亚高地人成功地报了杀叔之仇;另一个是戴蒙德已经过世的岳父,他曾有机会杀死一个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残杀了他所有亲人的凶手,但他最终把这个人交给了警方。可是,凶手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然后就重获自由。
在这两个故事中,一个人复仇成功,另一个人则放弃了复仇,这两种行为最终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虽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新几内亚高地的仇杀文化,但丹尼尔的复仇之举毕竟让自己的良心得到极大的宽慰,而戴蒙德的岳父在此后的60年里却一直生活在“悔恨、内疚的折磨之中”。显然,对于许多人来说,复仇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
我们总是倾向于将他人视作自身行为的主宰,如果有人对我们造成了伤害,我们会要求他承担责任,并认为这种罪行必须受到惩罚。而且通常来说,唯一合理的惩罚手段似乎就是让行凶者承受痛苦,或者剥夺他的生命。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一个以科学事实为审判依据的司法体制是否能够抑制这种复仇冲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够将人类行为背后的各种原因充分纳入考虑范围,这至少在一种程度上可以缓解我们对不义行为的自然反应。
例如,如果戴蒙德岳父的家人是被一头大象践踏而死,或者死于霍乱感染,那么我相信戴蒙德岳父所承受的痛苦会有所不同。我们也同样相信,如果戴蒙德的岳父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杀害他家人的凶手原本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而这个人之所以会犯下罪行,是因为大脑前额叶皮层受到某种病毒的侵害,那么他心中的悔恨也会缓解不少。
然而,复仇的“假象”仍然符合道德的原则,甚至是必不可少——如果它的确可以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对某些罪犯进行严惩(而非遏制或恢复)的做法是否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复仇的欲望,是因为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是自身思想、行为的绝对主宰,因此,复仇的欲望其实是建立在一种认知与情感的错觉之上,并由此产生出一种道德的错觉。
在探讨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有可能因为慑于事后的惩罚而中止实施时,我们才会将相应的原则运用到他的身上。我们无权让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行为负责。比如说,如果我们将打喷嚏定为一种罪行,那么无论面临的惩罚有多么严重,总会有人违反这条法律。然而,对于绑架一类的行为,实施者须要一步步地精心谋划,付之行动,因此威慑就有了用武之地。如果惩罚的威胁可以让你中止自己的行为,那么你的行为就恰好印证了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传统观念。
为了防止某些罪行的发生,严厉的惩罚也许真的是一种必要手段,而不能仅仅依靠遏制性或者恢复性的措施。但是,这种纯粹基于实用目的而采取的惩罚举措,与我们目前所实施的惩罚手段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如果对细菌与病毒的惩罚可以防止大规模传染疾病的发生,我们同样应该将它们绳之于法。
赏善罚恶的措施可以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要求当事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它甚至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社会惯例。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威格纳(Daniel Wegner)所指出的,自由意志观念可以成为理解人类行为的一把钥匙。如果一个人自愿选择在牌桌上挥霍掉一生的积蓄,我们会说他自作自受,这句话的含义是,他本来完全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他的一切行为都源于自己的想法。他之所以沉湎赌博,并非由于偶然的因素,也并非是受到某种幻觉的控制,而是出于他自己一步步的意愿、想法和决定。
在很多场合下,我们可以忽略那些潜藏在各种欲望、意愿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说基因结构、突触电位等等,而将关注重点放在有关人类行为的传统认识之上。当我们思考自身的选择与行动时,往往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一种合理建构自我思想、行为的最简单的方法。为什么我要的是啤酒而不是红酒?因为我喜欢啤酒。那为什么我喜欢啤酒昵?我无法解释,但我通常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在餐厅用餐的时候,我只要知道自己喜欢啤酒而非红酒就已经完全足够。无论原因是什么,反正相对于红酒来说,我更喜欢啤酒的口味。这其中是否存在所谓的自由?
显然没有。如果我决定违背自己的偏好去选择红酒,这是否意味着我神奇地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反常的决定其实与你自身的偏好一样,都根源于无法解释的因素。
节选自《自由意志》
湛庐文化策划出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