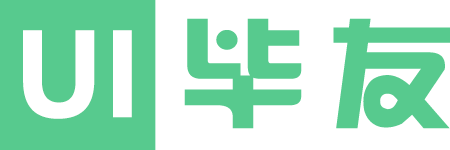(段永朝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推荐语:
“原来如此!”
作为一名曾就读于工业自动化专业的读者,我迄今清晰地记得,5年前在阅读诺布尔这部著作时,内心涌起的阵阵波澜。
20余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将“自动化技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之论,奉为圭臬。美国MIT的技术史教授诺布尔,用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在这部讨论技术发展的社会史著作中,展现了一幅令人始料不及的画面。
以“数值计算”方法为特征的自动化技术,之所以在众多技术中最终胜出,原来并非这项技术真的有如此多过人之处。决定性的因素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原来事关“车间的控制权之争”。
长期以来,技术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中扮演着重要、光辉的角色。技术的能量加上其笼罩的光环,往往成为“社会进步驱动力”的可信证言。诺布尔的这部著作,打破了这一神话。这无疑让“技术为了谁”、“谁拥有技术”等问题的回答,多了一个难得的视角。
这在电脑和网络的高科技依然占据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仍有巨大的警示价值。这个“警示价值”,我认为有三个层面,一个是由这本书作者的观点引申而来,简言之一句话:技术并非外界所了解、理解的那样,是“中性的”;另一个层面,是我自己的读后感,即长期以来我们被灌输的“技术进步论”,可能无形中给技术戴上了光环——包括信息时代的技术,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第三个层面是,既要防止狭隘的进步论的线性思维,又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阴谋论”(当前对待技术的态度,有一种“阴谋论”的暗流,是值得警惕的)。

另一种进步观
文/David F. Noble?译/李风华
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展现在我们面前时,谁都可以看见,生产力今天已然成为制造历史的力量。工业机器再次成为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中心,而追求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工艺则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推动力量。但正如这项研究所表明的,这些机器本身从来都不是生产中的决定性力量,它们仅仅反映了生产中的决定性力量。
在每一个时点上,这些技术进步都受到了各种力量的干预:社会统治权力阶层、全知全能的非理性幻想、具有合法性的进步观念以及技术工程本身与其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如果说——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与尤金?D?杰诺韦塞曾经这样写道——“历史不过是讲述谁统治谁并如何统治的故事”,那么,技术史也不例外。那种认为机器制造历史而不是人制造历史的技术决定论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对过于残酷而难以直接面对的现实给予了模糊的、神秘化的、逃避主义的以及息事宁人的解释。如果说施加在我们身上的社会变迁是不可避免的,那也是因为,这种变迁并不是遵从某种独立的技术逻辑,而是根据某种我们所有人都服从的社会逻辑。
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社会进程,而不是一种自动的超越性的决定力量,这可以解放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忽略了社会权势阶层的巨大力量),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个长期被否定的自由领域。它将人从技术逻辑的魔爪下解救出来,再次恢复了人作为历史真正主体的地位,而人的行为也不再如自然或形式逻辑所要求的那样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现在,技术进步本身只是被当成一个社会结构的产物,是一个新的变量,而不是第一原因,为人类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并预期多种未来的存在。此外,对技术进步的审慎检视显示,技术也可以通向两种不同的生活,其中一种服从设计者的意图与权势阶层的利益,另一种则完全相反——在技术设计者后面产生各种出乎意料的结果与不可预期的可能性。正如人类容易犯错一样,机器也不例外,不管最初的设计是如何完善、周全,自动化程度如何高。最后,如果技术进步是一个社会过程,那么它与其他社会过程一样,充满了冲突与斗争,而其最终结果总是无法预测的。
熟练劳动力短缺的困境
达尔文主义的进步观假定,如果商人引进一种新技术,这种技术必定是经济的。因为根据其逻辑,如果这种技术不经济,那么精于计算的商人或者会拒绝这种技术,或者由于错误地采用这种技术而破产。在此,技术的经济价值不是通过举证与细致的计算而得到估价,而是根据表面的商业行为来作为先定的理由。
这种观念浸染了对于“美国制造体系”——比如机器大规模生产——崛起的解释。它假定,降低竞争成本的动机与熟练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促使富有经济头脑的制造商研制开发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与资本密集型制造方法(专用设备、可互换零部件、标准化程序细致的劳动分工等),从而降低单位成本并减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它还进一步假定,这种资本密集型制造方法将比传统制造方法更经济,从而也是美国制造业成功的关键。
正如尤金?弗格森在最近的一篇史学评论中指出的,史学界开始对这一解释的事实与逻辑提出了质疑。保罗?乌泽尔丁是一位研究19世纪美国工业史的经济史学家,他认为,“绝不可以从理论的帽子中抓住一只历史事实的兔子。”
学者证明,降低成本并不是南北战争前工业进步的动机,而且熟练工人的供需情形在各地也不相同。虽然一些地区在某个时期缺乏熟练工人,但其他地区并非如此。弗格森还认为,美国制造业的成功,与其归功于昂贵而精密的设备的采用,毋宁归功于发明了“设计简单、制造轻便且有助于提高技术”的各类设备,它们的发明目的是节约“机器辅助制造下的手工加工”的时间,而且“正是技术的存在,而不是缺乏,构成了美国制造体系崛起的重要因素”。
尽管不存在确切的证据证明,人们所理解的熟练劳动力短缺实际上是推动自动化的一种重要动机,但它确实一再被提出作为自动化的借口。工业界不是研发足以扩大现存技术的机器——另一种补偿劳动力短缺的策略,并且在19世纪取得了成功——而是继续推进降低工人技能并从而取代工人的技术。《纽约时报》报告了1980年的机床展览会,并发现由于经理认为存在熟练劳动力短缺,他们“乐意耗资数千万美元来购买高度自动化的数值控制系统”。《纽约时报》指出,“展览会中最吸引眼球的场景”是“没有人操作的制造中心”——据称其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并解除熟练机械工短缺的困境”。
从一开始,自动化浪潮就源自于减少对熟练劳动力的依赖,降低工人的必要技能,从而削减工资。当代的培训方式完全符合这个总趋势。在一封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布莱尔机床公司的总裁表达了对熟练机械工短缺的关切,并呼吁创建一个“机械工学院”来增加其未来的供给。其立论根据就是熟练劳动力对于工业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人采取这一措施,建立机械工学院的呼吁被湮没无闻。相反,工业界根据自动化技术的要求,或者削减培训计划,或者重新安排培训方式以培训半熟练的工人。
这样,虽然工业界并不能增加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无论短缺是否存在——对自动化的强调仍然如故。与此相伴随的降低工人技能、削减工人职位并降低培训要求的做法,无疑实际上导致这样的短缺的发生——正如历史上的故事一样。这种人力资源的贫乏并非是自动化的原因,而是自动化的后果,但却被当成是进一步自动化的根据。这种循环论证主要依赖于其自身,此外还有社会的工业能力。
因此,自动化的经济理由——无论是作为动机还是收益——是无法让人信服的。此外,既然自动化并不是所谓劳动力短缺的唯一解决方案,也不是提高日见下降的生产率的充分措施,而在严格的技术意义上——它能否有效运转——它更不是必然可行的方案。新型设备的高昂成本(虽然计算机硬件的采购成本在逐步降低)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而随时出现的停机与维护成本——这反映出系统的不稳定以及全天候保持新设备运转的必要——更是让人头痛。运营费用仍然相当高,完全抵消了削减直接人工成本所带来的收益。
自动化的内在矛盾
此外,自动化方法本身也存在着内在的弊端。计算机制造要求所有的行为都必须转换成机器可读取的术语。形式化的描述、标准化的程序、代数式的整齐必须取代生产的人工与社会过程。虽然理论上美妙无比,但在现实中,这种宏大的抱负被证明是存在问题的。“每个人都认为可调加工方式是唯一的出路,”一名官员这样对《铁器时代》杂志说,“但美国并不只是有了可调加工方式就万事大吉了。”
“工厂的运营本来似乎非常有规则,但你要用计算机程序来描述它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财富》杂志的吉恩?比林斯基指出,“这时这些运营开始显出它的不规则性来。”这种问题在加工过程中无处不在,构成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的一个拦路虎。而金属切削业中有限的形式知识则使这个问题变得尤其突出,虽然自从弗雷德里克?泰勒以来,工程师们在这个方面已经探索了将近一个世纪。
现在尚不存在确定“科学的”方法来描述并充分预测刀具磨损、各类材料的“可加工性”,实际的机器性能以及经常改变的工作条件。当然,机械工与机器操作工每天都要遇到并处理这类意外情况,对付这些情况,他们所依赖的是他们积累的技能与经验。克服这些生产问题的最可靠办法就必须有赖于工人的合作。
管理层不是依靠工人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乞灵于所谓的自适应控制装置——所谓全面自动化的关键。“自适应控制”是一种通过使用精密的传感器、反馈装置甚至“人工智能”来让机器实现充分的自我纠错的做法。管理层希望采用这类自适应控制装置来自动对工作中的各种参数的变化做出补偿,从而使加工成为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自足的过程,仅仅接受远程的管理层控制。但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机床有了更多的诊断数据事实上更不稳定。”
一个机床研究小组最近指出,“在机器上安装多少传感器、监视器、计算器、警报器或者自动维修装置,事实上有个限度??人们越想通过引进附加装置来避免出错,就越容易出现更多的差错。”针对不稳定性而增加的复杂装置更加使得设备不稳定,而自适应控制也绝非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剂万用灵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适应控制能够克服各类加工问题,”研究小组得出结论道,但“在加工系统上增加部件与控制系统通常并不是一个取代初始设计与处理分析不足——或者为了实现控制与纪律——的良好途径”。很显然,追求“尽可能少的人工干预的做法是有极限的。”一名在军工试验室研究自动化的学生指出。
这样,我们又回到开始的地方,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有了这种经验,系统设计者与生产责任人终将认识到,他们那脱离现实的举措必将失败,并从而走上较为实际且更为确定的道路?至少在目前,我们没有理由抱着这样乐观的看法,因为人们认定,现在做出决策的人们在真诚地关心生产,并且以一种十分理性的态度从事。现实完全相反。如果这一宏大的抱负陷入了自身泥潭,它的支持者们将想方设法来掩盖事实,并且他们还找到其他方法来扩大他们的权力,延续他们的美梦。
结构性失业的幽灵
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库特?冯内古特就预测会有结构性失业这一挥之不去的幽灵,现在每个人都看到这一点。最近几年,对于技术性失业的恐惧,官方的通行口径是乞灵于技术推进的经济增长。人们被告知,技术性失业仅仅只是一种幻象,因为技术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远比它毁灭的多。具体来说,那些失去某型机器上的工作的人将会在该型机器的制造上找到工作。二战后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经济扩张、战争推动的间歇性工业“繁荣”以及政府大规模扩大对“服务部门”的资助,所有这些掩盖了就业错位的现象,吸收了大批失业者,同时也赢得了人们对于“增长”的认同。但现在这一招已经失灵了。
1983年3月,《商业周刊》承认,“令人大失所望的是,高科技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远远低于制造业所失去的就业机会。”比如,机器人制造业“预期创造3000-5000个就业机会”,而这些机器人本身“将导致50000名汽车工人失业”。杂志预测道,“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新产业的就业将只占到美国整个就业中的极小一部分。”此外,新产业规模较小,而且“高技术职位的增长与推进自动化的产业一样缓慢”——“未来将出现大量的无人工厂。”《商业周刊》警告道。
此外,许多新创造的职位还可能流入外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价格低,国家强迫执行工作纪律,而且工会是不合法的。《商业周刊》指出,制造商们由此越来越将它们的工厂设在外国的土地上。雅达利公司——科技乐观主义的政治象征——宣布将1700个职位搬到外国,这对它的支持者来说称得上是当头一棒,而惠普公司则“预测其海外工人的增长速度将高于美国国内工人的增长速度”。
对自动化的无歇止的追求已经造成了工人的失业与错位,与之相伴而来的是美国工业基础的普遍削弱,具体而言,技术的永久性流失。正如威廉?莫里斯针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后果所论以及刘易斯?芒福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再次重复该论断所表明的,在这个方面,社会所失去的远比它所得到的更多。它所蕴含的成本绝不限于生产,而且也具有深远的政治含义。
芒福德警告道,无歇止的自动化将逐步削弱小规模的、分散化的、以技术见长的、多样性的永久工业基础——这至少是民主的一个基石,是知识积累最可靠的载体,人类社会弹性与连续性的枢纽。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成的、大规模的、复杂的权威结构——既令人生畏同时也岌岌可危。芒福德宣称,在每个文明中,这两种工业结构都是同时并存的,如果说“权威”结构在生产物品与荣誉方面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那么“民主”结构则具备另一个优点:它长期生存。
反思我们的科技
自动化制造体系的推广者对他们的宏大工程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要他们能够利用公共经费尽情追求他们的梦想,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他们在社会财富中的份额与权力,他们就会继续忽略这种灾难性的前景,或者对此仍然一无所知。但是,工人从未抱有这种奢想。只有当他们的生存、组织、车间权力以及尊严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才再一次对自动化的危险发出警告。
最近,当公认的数值控制之父约翰?帕森斯建议暂缓所有的新技术开发,从而让社会吸收所有现存的技术,并集中精力对付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时,《美国机械师》的编辑警告他说,读者将认为他头脑不清。当然,这两个人并不是反对技术。他们只是希望在面对他们认为是疯狂的、无意识的、追求技术的浪潮时试图保持自己的理智。
从那些对他们的批评声来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人领袖与其他潜在的技术批评者极力避免被视为是技术进步的敌人。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真正的挑战:抵抗今天的技术进步,追求更人道、更民主的未来。这里不存在捷径,不存在万用灵药,也不存在任何的技术路径。
在另一个问题丛生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刘易斯?芒福德写了经典名著《技术与文明》。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芒福德试图——正如他后来解释的——在现代技术演进的恶劣现实与危险的趋势中“把握潜在的可能”。他拒不屈服于当时流行的悲观倾向,而是坚信技术进步中那偶尔被激起的乐观精神,并在满目废墟中寻求美丽的前景,并找到他称之为“新技术”的事物。
在他看来,这些技术清晰、有效、灵活,充满了人道气息,它建立在电子学、化学、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之上——在许多人看来,它与今天的高科技非常相似——将意味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但正如芒福德在30多年后自己所承认的,年轻的芒福德抱着这种不可救药的天真,在这方面梦想得太远。
我无意重复年轻时代的芒福德的错误,以另一种过时的技术超越奇迹论的错误承诺来维持自己的信念。相反,我的目的是支持更为冷静的老年芒福德的评价,即“获得这种技术的真正成就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变更整个体系的技术基础”。“这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芒福德提醒道,“只有人才能解决它。”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要求我们从根本上反思科技的形式与作用,反思建构更为民主、更为平等、更为人道、更具有创造性的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因此,仅仅是抵抗现有的技术进攻,即使还伴随着对那些权力执掌者的政治对抗,仍然是不够的。
“每个人都相信,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转型。”《商业周刊》最近报道说。今天没有一个人亲身经历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痛苦与骚乱。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如此自负地——甚至抱着极其幼稚的乐观态度——迎接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另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景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兴奋与期待——其中管理者们并不担心自己的工作,而是期待以工人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权威,技术狂则继续沉湎在不负责任的幻想之中,而军方则指望立刻实现总体控制的现实(或超现实),新进步主义政治家则满嘴讲着玫瑰色的言辞,这足以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人类的苦难与悲剧以及随后的群众暴动。
将现在的经济转型与19世纪的转型所做的类比往往只是完成了一半:灾难性后果被省略不计。更充分的对比将会带来震惊,让思想者停下来思考:那些受到损失的人将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后果会是什么?
目前而言,很少有人提出这些问题,更不用说回答它们。与此同时,自动化的冲动——受到新近燃起的竞争恐惧的激发——仍然不曾稍停。其结果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国家的工业基础不是复兴而是进一步被侵蚀;资源不是增长而是耗竭;珍贵的技能不是得到补充而是永久地消失;国家财富不是增加而是逐步损耗;不是民主与平等的扩展,而是权力的集中,控制的加强,特权的巩固;不是希望满怀的进步欢呼,而是失望不安的忧郁声音。
节选自《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感谢本文推荐人:段永朝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欢迎更多朋友推荐美文,小编代您与大家分享。
(毕友推荐——分享MBA推荐的文字。毕友推荐,旨在收集和整理MBA推荐的各类原创或转载的文章和资料,每日定期发布,分享给所有的朋友。通过每个人的推荐分享,实现大家单位阅读时间价值最大化。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请将您的推荐直接发至邮箱:2696039404@qq.com或Q:2696039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