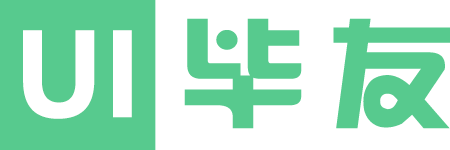毕友一言:
友情的崩坍,重于功业的成败,险过敌人的逼近。
无需想起,从未忘记
记得与电子科大的杜义飞教授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为何取名“毕友”?我说是取自“毕生的朋友”之意,他又问我,何为“毕生的朋友”?我想,毕生的朋友一定是真正的友情。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友情? 有这样两段文字,或许能够诠释一二。
真正的友情,心有灵犀,无关酒肉,无关利益,无关高低,无关贵贱,没有时空阻隔,是心灵的默契,是性情的相投,是灵魂的依附,是心心的通融。真正的友情,相知相识、相交相接,一如日月之行,无论风云变幻,终不减其辉映。
真正的友情,无须相从过密,不用推杯换盏,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利益交换,彼此之间无欲无求,心照不宣。真正的友情,一杯清水,一句口信,甚至一个念头,便可身心相托。真正的友情,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本周的“与自己对话”系列文章,我们将以“友情”和“朋友”为关键字,为大家推荐两篇文章,共赏共勉。
我们到底要交什么样的朋友? 文 / 林清玄
人生的朋友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一种是在他欢乐的时候不会想到我们,只在痛苦无助的时候才来找我们分担。这样的朋友往往也最不能分担别人的痛苦,只愿别人都带给他欢乐。他把痛苦都倾泻给别人,自己却很快忘掉。
一种是他只在快乐的时候才找朋友,却把痛苦独自埋藏在内心,这样的朋友通常能善解别人的痛苦。当我们丢掉痛苦时,他却接住它。
一种是他不管在什么时刻什么心情都需要与别人共享,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悲哀不如众悲哀。他永远有同行者,但他也很好奇、多事,总希望朋友也像他一样,把一切最私密的事都对他倾诉。
还有一种朋友,他不会与人特别亲近,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独自快乐、独自清醒,他胸怀广大、思虑细腻,带着一些无法测知的神秘。他们做朋友最大的益处是善于聆听,像大海一样可以容纳别人欢乐或苦痛的倾泻,但自己不动不摇。由于他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对别人的快乐予以鼓励,对别人的苦痛施以援手。
用水来做比喻,第一种朋友是河流型,他们把一切自己制造的垃圾都流向大海;第二种朋友是池塘型,他们善于收藏别人和自己的苦痛;第三种朋友是波浪型,他们总是一波一波找上岸来,永远没有静止的时候;第四种朋友是大海型,他们海纳百川,但不失自我。
当然,把朋友作这样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因为朋友有千百种面目,这只是大致的类型罢了。我们到底要交什么样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朋友?
纪伯伦在《友谊》里有这样两段话:“你的朋友是来回应你的需要的,他是你的田园,你以爱心播种,以感恩的心收获。他是你的餐桌和壁灯,因为你饥饿时去找他,又为求安宁寻他。”“把你最好的给你的朋友,如果他一定要知道你的低潮,也让他知道你的高潮吧!如果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才去找你的朋友,又有什么意思呢?找他共享生命吧!因为他满足你的需要,而不是填满你的空虚,让友谊的甜蜜中有欢笑和分享吧!因为心灵在琐事的露珠中,找到了它的清晨而变得清爽。”
在农业社会,友谊是单纯的,因为其中很少有利害关系。在少年时代,友谊也是纯粹的,因为多的是心灵与精神的联系,很少有欲望的纠葛。工业社会的中年人,友谊常成为复杂的纠缠,“朋友”一词也浮滥了,我们很难和一个人在海岸散步,互相倾听心声,难得和一个人在茶屋里谈一些纯粹的事物了。朋友成为群体一般,要在啤酒屋里大杯灌酒;在饭店里大口吃肉,一起吆喝;甚至在卡拉OK这种黑暗的地方,唱着浮滥的心声。
从前,我们在有友谊的地方得到心的明净,得到抚慰与关怀,得到智慧与安宁;现在,朋友反而使我们混浊、冷漠、失落、愚痴与不安。现代人都成为“河流型”“池塘型”“波浪型”的格局,要找有大海胸襟的人就很难了。
在现代社会,独乐与独醒就变得十分重要。所谓“独乐”是一个人独处时也能欢喜,有心灵与生命的充实,就是一下午静静地坐着,也能安然;所谓“独醒”是不为众乐所迷惑,众人都认为应该过的生活方式,往往不一定适合自己,那么,何不独自醒着呢?
我们只有能独乐、独醒,才能成为大海型的人,在河流冲来的时候,在池塘水满的时候,在波浪推过的时候,我们都能包容,并且不损及自身的清净。
严重的友情 文 / 余秋雨
友情这件事,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表面上,它是散落四处的点点温馨。平时想起一座城市,先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初到一个陌生地,寂寞到慌乱,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朋友,那么,时间和空间就会在刹那间产生神奇的蜕变。两个朋友见面时再夸张的动作声调,四周路人都能原谅。有时久违的朋友会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时从背后狠狠地擂过来一拳,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轻,但奇怪的是我们还没有回头就能感觉到这种分量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总是满脸惊喜,然后再转身寻找。我们走在街上,肩膀和后背总在等待着这种拳头。等了半天没等到,空落落地走一路,那才叫无聊。
我一再对学生们说,你们年轻,奋斗吧,追求吧,去创造什么事业吧,但请记住,一过中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朋友们活着了。各种宏大的目标也许会一一消退,而友情的目标则越来越强硬。报答朋友,安慰朋友,让他们高兴,使他们不后悔与自己朋友一场。所谓成功,不是别的,是朋友们首肯的眼神和笑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企盼着它们,而不是企盼那没有质感的经济数字和任命文本。我们或许关爱人类,心怀苍生,并不以朋友的圈子为精神终点,但朋友仍是我们远行万里的鼓励者和送别者。我们经由朋友的桥梁,向亿万众生走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居然能兼济天下。
如此说来,友情确实重要,但又怎么说得上“严重”呢?
严重的是,我们无法辨别这一切的真伪。
如果,我们长期所信赖的友情竟是虚假的,而这种虚假又并不出于恶和罪,而是出于友情本身的悖论,我们将如何面对?
友情的崩坍,重于功业的成败,险过敌人的逼近。
我曾在澳洲墨尔本西南面三百公里处的海岸徘徊,产生过对这一问题的恐惧联想。在那里,早年异域的船只极难登岸,高耸的峭壁不知傲视过多少轰然而毁的残骸,但终于,峭壁自己崩坍了,崩坍得千奇百怪,悲凉苍茫。人世间友情的崩坍也是这样,你明明还在远眺外来的危险迹象,突然脚下震动,你已葬身大海。
也有拼死不愿崩坍的,当周围的一切高度都被海水卷走后,它们还以孤峭的残柱挺立在汪洋之间,成为墨尔本海岸的一大景观。这些残柱宛若悲剧英雄的形态,旅游者们称它们为“十二门徒”,远远看去确实很像,长风残照下一个个独立在大海中,宣告着门徒们对师道的忠诚,对友情的挚守,宣告着一切崩坍总有例外,实在让人感动。但这些门徒互相不能靠近,不知哪个夜晚在激浪的冲击下终于站不住,冲走一个,再冲走一个。在它们近旁,已有很多逐一被冲走的先例。我看着这些残柱,心想人世间最具有造型意义的友情佳话,会不会也只是一种苍茫大海间临时的孤傲?
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平淡,不一定能遇到友情全方位崩坍的机遇,因此完全无法验证立足的友情地基是否坚实。不知道它有岩脉连着地壳,还是仅仅泥垒沙积?有时也想,既然没有海浪,那么不坚实的友情地基也就不存在危险,何苦对它过于挑剔?但立即否定了这种宽容,因为这块自己多年选择的友情地基,正是自身精神的寄托所在,把有限的生命寄托于一种潜在的危险,这不成了一种自我欺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警惕了。友情的话题虽然处处可以听到,但它的实质性含义却让人不敢靠近,不敢逼视,不敢细谈。相识的人们聚会,最轻松的说法是“叙叙友情”,其实到时候谁也不会真的叙什么友情,大多也就是回忆一下过去,胡聊一些家常罢了,友情如此艰深,哪能随便叙得了的?
友情的某些真相,即便随口谈起,也会把善良人吓一跳。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这样记述柔石:“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这位柔石,是一位不怕死的人,他对自己随时可能被敌人杀害并无惊疑,却惊疑于世间居然有人“卖友”、“吮血”。这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叛卖友情比牺牲生命更不可想象。我想,只要他们固守的友情不侵害人类的基本原则,这样的人基本上都可进入“君子”的范畴。倒过来,另有一些人,把友情看作小事一桩,甚至公然表明自己如何为了某个目的而不得不糟践朋友,我真为他们可惜,因为他们不知道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们在世俗人心中的形象就永远难于修复了。
一切真正成功了的政治人物一定会在友情上下大功夫,否则他们不可能吸引那么多人手提生命跟着他们奋斗。但是,他们果真在友情上如此丰盈吗?远远未必。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失势,在友情上往往特别荒凉。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深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他们一生的功绩大部分抵消。有的政治人物在处置友情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但越是这样越容易失去友情的平等本质,他们握在手上时松时紧、时热时冷的友情缆绳,其实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友情。为此,我在前两年读到一位华裔美国历史学家的论述时眼睛一亮,他论及中国现代一位重要政治家,说再过多少年,这位政治家至今无法被人们原谅的严重错误也许会被历史学家们原谅,将来的历史学家们永远无法原谅他的,可能只有一点:作为男人,他对不起很多朋友。
不必到今后,这话今天来说也已经有广泛感应。这位气吞山河的政治家居然没有想过,再惊人的功业也不足以成为当众背弃一位老友的理由,除非这位老友实在不堪到了非被背弃不可的地步。他伟大到已经不在乎友情,但显而易见,他错了。
他身边,一位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他的政治家却受到人们更多的怀念,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位政治家有时比较把友情当一回事。怀念他的人并不认识他,但友情是人世间最敏感的部位,再远的事情一旦与友情相连,即能触及万众痛痒。千年前的一次小小的卖友举动,如果留下了文字记录,也会引起千年后的痛苦和愤怒,更不要说当代人了。
从历史看,除了少数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适宜与过大的权势、过高的智慧连在一起。有时,高贵的灵魂在关爱天下时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友情等级和友情秩序,结果总是吃足苦头。它是一个最容易被处于得意状态的各个方位误认为早已圆满解决而实际上远非如此的真正的大问题。
记得八九年前我写过一篇《上海人》的文章,分析了上海人的生态和心态特征,一时产生不小的影响,但也有不少外地读者来信,说我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上海人对友情的奇怪态度。其中有一位说,据他观察,上海人是最喜欢哄聚在一起又最不讲友情的一群;还有一位读者说,上海人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熟人,上海人不懂朋友的深义,因此没有真正的朋友。对这些读者来信我没有理会,因为我的朋友虽然各地都有,但较多的还是上海人,我一时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体验。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才恍然大悟。在友情上发生的事件,是很难说得清又很不愿意说的,因此我直到今天没有对此事发表片言只语的声辩,不过从那时起,我对上海人某一阶层的群体心理素质产生了另一种评价。
所不同的只是,我突然理解了许多在友情问题上欲哭无泪的诉苦者,而在以前,我总是劝他们别误会,别过激,别把人心看得那么坏。
“您简直无法相信,当我专程到北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追查谣言的根源,结果是,全部谣言出自每星期与我见面吃饭的三个朋友!”
我凄然一笑,深深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