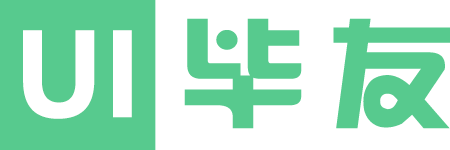【毕友导读】1980年,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iaw Miiosz 1911-2004)由于“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的创作继承了波兰古代诗歌和浪漫主义传统,同时汲取了现代不同流派的长处。他主张诗人应当用朴实的语言反映真实,摈弃言之无物的华丽辞藻。在风格上他的诗歌自然、流畅,寓意深刻,为举世公认的诗歌大师。本文摘录了米沃什晚期创作的部分诗歌作品。
准备
还需一年的准备。
昨夜我开始着手撰写一部大书,
其中我的世纪将如其所是地出现。
太阳升起照临正直也照临邪恶。
春和秋将准确无误地往返,
荆棘鸟在灌木丛用粘土建造它的巢穴,
狐狸将学会它们狐狸的本性。
这便是主题,还有别的。比如:军队
迅速穿过冰封的平原,在众声合唱中
夹杂一句咒语;坦克火炮
在街角显得巨大无比;黄昏时一支骑兵
驰入带了望塔和铁丝网的军营。
不,不会是明天。而是五年或十年之后。
关于母亲们我依然想得太多,
想要知道诞生自女人的人到底是什么。
当沉重的军靴踢着他时
他卷缩着,护住头;身上起火,奔跑,
被烧起耀眼的火焰;推土机将他扫入一个土坑。
她的孩子。曾经怀抱一只玩具熊。在狂喜中被孕育。
我还没有学会平静地讲话,如我应该的那样。
自白
主啊,我爱草莓酱
爱女人身体黑色的蜜甜。
冰镇伏特加,油鲱鱼,
桂皮、丁香的,香味。
我能是何种先知?圣灵怎会
光顾我这样的人?另有
许多人,他们堪当此名。
谁会相信我?人们见到的,是我
享用美食,倾尽酒杯,
贪婪扫视女招待的颈子。
不足并自知。渴慕伟大,
对于其品性,虽不十分,
幸能以部分的洞见分辨,
深知,留给渺小如我者,唯有:
短暂希望的盛宴,骄傲的愈挫愈奋,
一种驼背者的饰物,文学。
而书籍依然
而书籍依然会在书架上,独立的存在,
一旦出现,便会保持湿润
仿佛秋日树下闪亮的栗子,
被触摸,悉心照料,开始生存
而不顾地上的火,风蚀的城堡,
边地的部落,运动中的星球。
“我们存在,”它们说,即便它们
被一页页撕去,或者为嘶嘶作响的火舌
噬尽文字。比起我们
远为经久,我们微弱的温度
那么容易随记忆冷却,发散,消失。
我想象我不再存在的地球:
无事发生,没有损失,依然是个陌生的舞台,
女人们的衣饰,带露的紫丁香,山谷里的歌声。
而书籍依然会在书架上,出生高贵,
衍生自人,而同时也衍生自光源,高度。
窥淫狂
我曾是游荡在这大地上的一个窥视的汤姆。
银河的气泡内部咕咕作响并发酵。
她的帽子有着淡紫色的花朵;她穿绣花边的短裤。
我们共餐于日影点缀的桌布前。
或者,她的乳房半裸于帝国式女服间。
我愿变作一件连衣裙,佩带某级纪念章
以便能想象它们变硬的乳头。
我总在寻思女人们隐藏起来的一切:
那簇拥的荷叶边、褶皱和裙子,
知识花园的黑暗入口。
有一天她们死去,同去的还有她们各式的丝绸和镜子,
公爵夫人,公主,侍女。
想到她们是那样美丽,
也会轮到她们腐烂,我喉咙哽咽。
说真的,我并不曾渴望与她们做爱。
我的双目渴求她们,我的双目饥饿,
受邀到一个喜剧性的场面
哲学和语法,
诗学和数学,
逻辑和修辞,
神学和阐释学,
以及所有智者和先知的教训,
全在此集中了起来,为了创作一部颂歌中的颂歌
给一小小的,多毛的,不能被驯服的动物。
处方
一切都行除了忏悔。我的生命
令我如此不安,也许我可以
在对它的讲述中找到安慰。而我将被理解
被那些不幸者——他们何其多!——他们摇晃在
城市的大街,吸过毒或者醉熏熏,
染上记忆的麻疯病,为生活感到内疚。
什么压抑着我?羞耻
为我自己的不幸不够独特?
或者相反。哀诉已经成为时尚,
不快乐的童年,挫伤,以及所有别样的痛苦。
即便我早已预备好了约伯式的抱怨,
最好缄默,去赞美永恒
事物的秩序。不,另有其物
限制着我开口。任何不幸者
都应成为一个真相的讲述者。应该?如何,
带上全部的伪装,趣闻,自怜?
虚伪的情感导致虚伪的言辞。
我过于看重风度而不愿担此风险。
在黑色的绝望里
在灰黯的怀疑和黑色的绝望里,
我草草写就献与大地和空气的赞美诗,
佯装欢乐,尽管我缺少。
年龄已使哀歌过剩。
于是问题来了——谁能回答——
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还是一个伪君子?
湮没
并非每个人都会被赋予一个真实的晚年。
它的财富乃是
对于肉体之骄傲的沉思,而它一旦
在我们体内涌现,我们还是我们但已全然不同。
它真是全然喜剧性的:
在一面镜子前整理头发,
担心帽子与脸型是否匹配,
以舌尖濡湿嘴唇,
将口红迅速涂上,
打上领结,以一种百兽之王的神情。
大地之灵,他是如何捉弄我们!
如果个体不过形式,种属才有意义,
正如邓斯·司各脱*似乎相信的,
我们不过完成了我们被要求与注定被湮没的
一切,一如有人附耳所说的那样。
然后,在幻像中,一个假想的城市升起。
在它哥特式的塔顶之间燕子飞舞。
一个老年人站在窗前
他已见过许多的城市,
几乎自由了,他大笑着
却没有重返任一地方的打算。
得克萨斯
我从得克萨斯返回。
在那里我朗诵了我的诗歌。
没有什么地方像在美国给予诗歌朗诵那样高的报酬。
挨着签名我写上日期2000。
老年缠上我的双脚仿佛粘稠的沥青。
头脑抵制着,但头脑即意识。
我能拿它如何,能够向谁展示?
最好是什么也不说。
我已体验幻觉的羞耻,爱、恨、热望、苦斗
的记忆的幻影。
如今我几乎不能相信
我已勉力度过了我的一生。
我的秘密
我所有痛苦的秘密
都将,一个一个地,显露。
多么贫乏的人生!他们会说,
道路却多么陡峭!
我从让娜·赫什*所学到的
1.理性乃上帝所赐,我们应该相信它理解世界的能力。
2.那些人,试图以阶级斗争,力比多,权力意志——取代理性的力量,动摇我们对于理性的信任,他们错了。
3.我们应该懂得我们的存在封存在我们认识的范围之内,而不应将现实归之于头脑的梦想和幻觉。
4.真理乃是自由的证据,奴役的标志不过是谎言。
5.对于存在适当的态度是尊重,因此我们必须远离那些用嘲讽来贬低存在而赞美虚无的人。
6.即使我们被指傲慢,真实的情况却是:心灵生活依据严格的等级制。
7.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普遍浸染了高谈阔论的恶习,亦即不负责任的清谈。
8.在人类活动的等级里,艺术高于哲学,而坏的哲学败坏艺术。
9.客观的真理依然存在;即,在二种对立的主张中,一为真,一为假,除非在严格限定的情况下,当维持矛盾性为合法之时。
10.与任何宗教派别的命运无关,我们理应保持一种“哲学的信念”,亦即作为一种人性尺度的对于超越性存在的信仰。
11.时间只会剔除那些,在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之后,被证明无益于提升文明大厦的一切人工和心灵的产品并将它们判与遗忘。
12.在我们的一生中,不应因我们的错误和罪愆屈从于绝望,因为过去决不会被取消,过去只会因我们接下来的行动获得它的意义。
论诗人之死
语法之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现在去词典的树丛和原始森林搜寻他吧。
反对拉金之诗
我学会了带着绝望生活,
而菲利普·拉金突然出现,
解释着为什么说所有生命都可厌憎。
我没有明白为何应心怀感激。
呼一口气已很艰难,
即便没有他那关于虚无的虚张声势。
我亲爱的拉金,我知道
死亡不会漏掉任何一个人。
但这并不是一个像样的主题
无论是对于挽歌还是颂歌。
论人类的不平等
那并不真确:说我们不过一团肉体
时而咕噜几句,时而移动,渴求。
那些在海滩上赤身裸体的人错了;
那些在地铁自动梯上的人群也不对。
我们并不知道那紧挨着我们的是谁。
他也许是一位英雄,圣人,天才。
因为人类的平等是一个幻觉
那些统计学表格只是一些谎言。
在人类日新的等级存在中,
我只遵从内心崇敬的冲动指引。
我行走于某位被选中者骨灰掩埋的地方,
尽管它们不会比其他人的骨灰更为长久。
我承认我内心的尊敬和感激,
没有理由为这些高贵的情感羞愧。
但愿我能证明我配得上与之相伴,
追随他们,攥着王者之服的褶边。
阅读安娜·卡米恩斯卡的日记
读她,我意识到她是多么富有而我是多么贫乏
爱与痛苦,哭与梦想与祈祷她都是多么富有。
她生活在自己人中间他们并不幸福但彼此帮助,
维系于生者与死者间的契约并在墓前续订这契约。
香草,野玫瑰,松树,土豆地,令她高兴
还有自童年就熟悉的,泥土的香气。
她不是一名卓越的诗人。而这才是关键:
一个善良的人不必懂得那些艺术的把戏。
后继者
请听,年轻人,或许你会听到我的声音。
正午。蟋蟀歌唱,就像一百年前
它们为我们所做的一样。白云掠过,
影子移动在底下,河流闪亮。
你赤裸裸降生。一种你感陌生的
语言的回声,在这里,在空气里,
我们的词语向你讲话,温和而无辜
犹如闯入者之子。你不知道
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你不寻求
曾在这里为人信奉的希望和信念,
你走过一堆碎石,一些写着名字的纸片撒落其间。
而这日光下的流水,菖蒲的香气,
发现新事物时相同的狂喜
联结起我们。你将再一次感到
他们试图永久驱逐的神圣。
某种东西正在返回,无形,微弱而羞怯,
怀着崇敬,没有名字,但无惧怕。
在我们的绝望之后,你最为热切的血,
你年轻而渴求的眼接替了我们。
继承人。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请听,再听一次。回声。微弱的。越来越微弱的。
采杏
日光里,那边,底下,海湾那儿
薄雾之云游荡,转瞬即逝,
蓝天下的山峦一片灰蒙蒙,
杏树,结满果子,黑黝黝的叶子,
闪着微光,黄和红,让人想起
赫斯珀里得斯①的花园和天堂的苹果。
我伸手摘取,突然感到精灵就在面前
于是将篮子放到一边,说:“可惜
你已离去不能看到这些杏子,
而我庆祝着这不值得的生命。”
(评论)
天啊,我没有说我应说的话。
我将雾霭和混沌交予了蒸馏装置。
那存在或非存在的王国
却常常与我同在,以千百次的
召唤、尖叫,抱怨,让我听到,
而她,我所面对的唯一之人,
也许只是一个合唱队的领唱。
那仅只发生一次的,并不停留于词语里。
国家消失,还有城市和环境。
无人看到她的面孔。
而形式本身,总是意味着背叛。
无题
夏威夷羊齿草巨大手指似的叶子
在太阳和我的欢乐衬托下,
想到在我不在人世时它们仍将存在。
我尽力抓住这欢乐所示的一切。
晚安
没有义务。我并非一定得深奥。
并非一定要艺术地完美。
或崇高。或富于启示。
我只是漫游。我说:“你一直跑着,
这就好。那才是应做的事。”
而现在缤纷世界的音乐改变着我。
我的行星进入一个不同的房子。
树和草坪更加与众不同。
哲学一个接着一个过时。
一切都更轻了但不乏离奇。
果酱,葡萄佳酿,珍馐名馔。
我们聊了一会儿辖区内的集市,
乘华盖马车旅行身后的一片黄尘,
江河一度如何,菖蒲的香气又怎样。
这比细究一个人的私梦更有意思。
就这样时间到了。就在这里,看不见。
谁知它是怎样抵达这里和别处的。
让别人去对付这问题吧。是我逃学的时间了。
Buena notte.Ciao.晚安。
十二月一日
在这个季节,葡萄园的乡下一片赤褐,微红,洋红。
山峦蓝色的轮廓呈现在一道富饶的河谷上。
太阳未落山前是温暖的,背阴处寒气返回。
一阵强烈的桑拿浴后游泳,在一个树林环抱的水池。
黢黑的红杉树,透明的、有着苍白叶子的白桦树。
在它们精致的网络里,一轮月亮的薄片。
我描述这些因为我懂得了怀疑那些哲学
那尚存的一切才是真实的世界。
我的青春之城
无人生活它也许更高雅。生活就不高雅,
他说,多年之后
回到他青春的城市。无人健在
那些曾一起走在街上的人。
如今他们一无所有,除了他的双眼。
踉踉跄跄,他代替他们,走着瞧着,
在日光下他们相爱,在重放的丁香花下。
他的双腿,比起那些不存在的腿
毕竟完美得多。他的肺呼吸着空气
就和生者一样。他的心脏跳动着,
并以其跳动令他吃惊,在他体内
他们的血液流动,动脉为他们提供氧气。
他感觉到,他们的肝,脾,肠,在体内。
男性和女性的特质,消失了,又聚于他一身,
以及所有的羞耻,痛苦,爱。
如果说我们同意有过什么启示
他想,只是在一个同情的时刻——
当分开他们和我的事物瞬间消逝
当一串丁香花上洒落的阵雨
在同一刻落向我的,她的,他的脸。
草地
河边茂盛的草地,在干草收割之前,
在六月阳光下一个纯净的日子。
我搜寻着,找到了,一眼认出了它。
自童年就熟悉的青草和花朵生长在那里。
我半睁眼睛承受着明亮。
这芬芳之气容留了我,一切知识不复存在。
蓦然间我感到我正在消失并快乐地哭泣。
在加勒比海一座岛上翻译安娜·斯维尔
在香蕉园附近,在甲板椅上,靠近游泳池
在那里,卡罗,赤裸,以自由或
古典式风格划动着两腿,我打断她
为了问一个同义词。然后我又一次沉浸在
私语般的波兰语里,在沉思里。
因为思想和身体的短暂性,
因为缘自我们共同命运的你那温柔的拥抱,
我唤你进来而你将来到人们中间,
虽然你在诗中写过:“没有我。”
“多么快乐,没有我。”
它并不意味:“我不存在,”
或“Je n’existe pas”①,而是纯粹的斯拉夫语:
“Mene netu”, 有点东方化。
而且,的确,通过赞美存在:
做爱时抚摩的愉悦,海滩上漫跑的愉悦,
在山中漫游的愉悦,在倒伏的干草上行走的愉悦
你消失了,为了存在,非亲身地。
最后一次见到你时
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你
也不喜欢你的诗。一头那样长而密的白发
你可以骑上扫帚,将一位魔鬼引为情人了。
而你自负地宣称着
你的脚趾、脉搏、大肠的哲学。
诗的定义:无论我们做什么,
欲求,爱,占有,受苦,
总是只有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一定存在别的什么,真实而稳固。
尽管无人知道永恒是什么。
而身体是最神秘的东西,
尽管,它是那么易朽,却意欲纯粹,
从那大叫着“我”的灵魂获得解放。
安娜·斯维尔,一个玄学诗人,
倒立于头顶时,她感觉最好。
告别我的妻子雅尼娜
送葬的女傧会把她们的姐妹交给火焰。
火焰,与我们在一起时看过的一样,
她和我,在婚姻里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为美好或邪恶的誓言维系,冬季
壁炉的火,野营的篝火,燃烧的城市的火,
元素的,纯洁的,来自创世之初的火,
将带走她飘动的,灰白的,发,
攫取她的双唇和颈项,吞没她,那
在人类的语言里标明爱的火焰。
我思无所思,关于语言的事。或祈祷的词。
我爱过她,却不知道真实的她是谁。
我带给她痛苦,追逐我的幻影。
和女人们一起时我暴露出对她的背叛,但我只忠实于她。
我们共同生活历经了太多的幸福和不快,
分离,奇迹般的获救。而现在,剩下这灰烬。
而海水冲激着海岸,当我走在空空的林荫道。
而海水冲激着海岸。平常的悲哀。
如何抵抗虚无?什么力量
会保存曾经的一切,如果记忆不能长久?
因我只记得一点点。我记得的是那么少。
的确,重生的时刻意味着那被一日日
延迟的最后的审判,也许因为主的仁慈。
火焰,自重力的解放。苹果不会落下,
山不会从其位置移动。在火帘之外,
羊羔站立在不可摧毁的草地。
炼狱里的灵魂燃烧。仿佛已疯狂,赫拉克利特,
看到世界的基础在火焰里耗尽。
我相信肉体的复活么?而不是这堆灰。
我呼唤,我哀求:所有元素,你们分解吧!
以另外的形式升起,让它来吧,王国!
在这尘世的火焰之外重新创造你们自己!
致杨·勒本斯坦
当然我们有太多共同之处,
我们在巴罗克城市长大
无须问是什么国王建造了教堂
什么王子住在那座宫殿,建筑师和雕刻家
叫什么名字,来自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什么作品使之闻名,
我们打发时日,宁可在华丽的廊柱前打球,
跑着经过那些飘窗和大理石阶,
然后,公园浓荫下的长椅比头顶
一尊石膏天让我们觉得更亲近。
还有什么保留下来:对扭曲线条的爱好,
形如火焰的,反转上升的螺旋线,
用丝绸衣服盛装我们的妇女
活跃骷髅们的舞会。
和她在一起
我母亲那可怜的多瘤肿胀的膝盖
在一个不存在的国度里。
在七十四岁生日我想到它们
在伯克利圣玛利·玛格达琳教堂望弥撒时。
仪式上读了一段《智慧书》
关于上帝没有制造死亡
也不高兴看到生命的湮灭。
读了一段《福音书》,马可关于
一个小女孩的话,他对她说:“Talitha,cumi!”
这话也为我说。使我从死者中站起
重复那些在我之前生活的人们的希望,
在与她的恐惧的合一中,带着弥留之际的痛苦,
在靠近但泽的一个村子,在阴暗的十一月,
沮丧的德国人,老男人和老女人,
来自立陶宛的被疏散者都可能感染斑疹伤寒。
和我在一起吧,我对她说,我的时间已不多。
你的话成了我的,在我内心深处:
“一切都似乎表明只是做了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