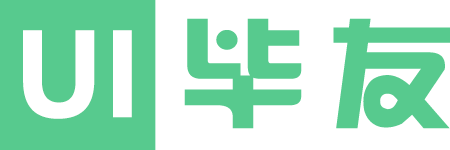【毕友导读】:本文由北京大学四川校友会秘书长段琳先生推荐。18大以后,国人普遍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呼唤思想上的一次新启蒙,以做好理论上的准备。这就必须对以往曾经有过的启蒙进行一番反思,并为这场新的启蒙探索方向……

【段琳推荐】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
18大以后,国人普遍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呼唤思想上的一次新启蒙,以做好理论上的准备。这就必须对以往曾经有过的启蒙进行一番反思,并为这场新的启蒙探索方向。
一、对前两次启蒙的反思
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新启蒙”运动。这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凶猛,舆论也造得轰轰烈烈,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不久就消沉下来,甚至反过来遭到批判和清算。只有当政治上国人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有了整整一代人的新的记忆,人们才发现启蒙仍然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
中国20世纪的启蒙运动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两场启蒙运动都是由某些民众的监护人,或者说“知识精英”们,居高临下地对民众进行“启蒙”或“发蒙”,把民众当儿童来引导和教育。而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种含义恰好就是知识精英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之所以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是因为知识精英们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了一整套的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他们一方面自己还没有经过真正彻底的启蒙,因为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得出这些价值原则,从学理上探讨这些观念的来龙去脉,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而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另一方面,他们眼中的民众也仍然只是受他们教育的未成年的儿童,民众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是非,只须跟着他们去行动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推进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这些自认为是“启蒙”的思想家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启发群众、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时,他们已经在做一种反启蒙的工作了,并且总是以盲目追随的群众的人数作为自己的“启蒙”成就大小的衡量标准。这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什么总是特别关注那种表面的“轰动效应”和政治效果,而很少深入到理论本身的缘故。
所以,20世纪第一次启蒙运动很容易地就被“救亡”的政治要务所“压倒”(李泽厚)。这首先是由于启蒙价值在完成这一要务上显得不如传统的东西更中用,更应急,更能立竿见影;其次是由于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按照同一个“启蒙”的逻辑而走向了大众崇拜甚至愚昧崇拜的不归路,以新的造神运动来“启”群众之“蒙”,让群众陷入幼稚就是美、盲从就是力量、愚蠢就是“觉悟高”的幻觉。
第二次即80年代的启蒙运动虽然摆脱了“救亡”等政治要务的干扰,而在历史和文化的层面比前一次启蒙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但在对于普遍人性的反思方面仍然未达到西方启蒙运动的深度,只有一些道德化和情绪化的批判,而极少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对西方价值观进行普遍人性层次上的反思和追溯。这些启蒙者不过是“西化派”而已。第二次启蒙的总体倾向是知识精英眼睛向上,希望自己的大声疾呼能够在民众中引起轰动后,最终被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听进去。如果说它也代表了人民说话,它代表的也只是人民群众对于领导和政策的一种消极的等待、期望和焦急的心态。当然,这种启蒙的批判总比什么也不做、甚至复古倒退要好,然而,它并没有在理论上从人性的普遍本质中获得有力的支持。
因此,进入90年代,启蒙的声音就忽然沉寂了,因为人们只是把启蒙看作一种技术性的方法,而中国的问题似乎还是要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解决。启蒙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人性中一个必要的层次,这样的层次即使被超越、被扬弃,也还是不言而喻地保有自己公认的价值;相反,它被人们再一次地作为无用之物而抛弃了。反观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那些鼓吹启蒙思想的精英们几乎无一不想借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观念在现实社会中“解决问题”,有种急功近利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倾向。在这方面,五四的启蒙先驱者们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民族危亡确实是当时每个中国人所惟一能够考虑的头等大事。但是,时至80年代,启蒙精英们仍然怀着同样的心态去用过激的言词刺激大众的神经,极力造成某种轰动效应,而疏于反省政治层面底下更深层的文化心理问题和人性问题,这就是一种误导了。启蒙思想在他们那里除了具有清算以往的封建残余思想的功能以外(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为当前的政策提供参考,为改革开放设计蓝图(在这方面他们一败涂地)。
中国20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通常都自认为自己所把握到的真理是绝对的,凡与自己意见不合的都是应当打倒的,并因此而上纲上线,热衷于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由于这些人其实都是手无实权的一介文人,所以在他们之间倒是应当提倡宽容,应当在自由讨论的空气中把问题深入到学理的层面。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要做到这一点还的确不容易的话,那么至少80年代的启蒙就应当更多地朝这个方向努力。但遗憾的是,不论哪个时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更像是一些谋臣或智囊,而不像卢梭和康德那样一些隐居起来思索人性问题的人。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效,所以他们都把衡量理论的绝对标准置于现实社会政治的可行性之中,借用政治操纵来杜绝启蒙思想本身进一步发展和自我超越的余地。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充满了过激心态及对政治权力的诉求,而缺乏宽容精神。
进入到21世纪,启蒙理想被中国人的“国学热”所“超越”,这毫不奇怪。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惯性就在于把停滞不前和倒退当作超越,甚至把腐朽当神奇。中国启蒙从五四以来就在启蒙的大门口徘徊,包括80年代的新启蒙也不过是旧话重提,每次都是转一圈又回到原地,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们只是把启蒙理解为一场“启蒙运动”,运动过后,我们“没有出路”,只有退回传统,反启蒙。
中国当代启蒙之所以老是停留于启蒙的门口,是因为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启蒙混同于中国传统的叛逆思想,如老庄隐士、魏晋名流、明清异端。这股源远流长的思潮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潮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他们反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五四启蒙思想正是从这一点切入而使当时的一大批“新青年”趋之若鹜。但毕竟,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如果没有普遍理性作为平台,而只是一种个人气质和“性情”,甚至只是青春期的一种生理骚动,它就不能内化为人性中的一个必然的层次,而只是一阵过眼烟云。等而下之则堕落为物欲横流。这样一种“启蒙”,的确“没有出路”。
鲁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当年也曾作为“新青年”而狂热过,但热潮过后,陷入低潮和颓废,为生计只好到乡下去教《三字经》,成为一个“无可无不可”的虚无主义者,与“启蒙”之前一样的缺乏理性。鲁迅本人也正是在这方面有其不足。五四的启蒙和西方启蒙相比一开始就面临着先天不足,不像西方启蒙有古希腊理性传统作铺垫。我们用来嫁接西方启蒙的“砧木”只能是古代狂狷之士的自然性情,它没有自身的积极建树,注定要由儒家正统来收拾。80年代新启蒙同样也是这个问题,它最终走向复古倒退是必然的。
中国20世纪两次启蒙都未对启蒙的真正含义领会和吃透,而是浅尝辄止,抓住了启蒙运动的一些表面的可操作性的口号,把它转变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治国方略或策略。这样,任何口号都无法改变中国传统几千年既定的格局,这些口号甚至可以被利用来大搞专制主义复辟,如“文革”的“大民主”和大批“孔老二”。今天没有人认为“文革”也是一场启蒙,相反,它正是“新启蒙”所要反思的主要对象。
而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国情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知识精英们的大声疾呼在底层民众中找不到什么回应,因为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基于自然经济之上的小农生活,他们的人格没有独立,他们渴望一个皇帝或高高在上的精英来给他们掌握方向、稳定人心。
但是,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几千年传统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乡离土,进城打工,城市化成为整个国民生活的重心。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靠传统那一套方式已经完全无法解决,而必须引进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普遍原则,包括市场经济的运作规范、配套的政治体制形式以及伦理道德中的普世价值,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而这就需要考虑中国当代社会的第三次启蒙。
二、第三次启蒙的特点
第三次启蒙正在发生中,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是少数知识精英从国外引进一套最新知识体系,来改造中国的社会文化,而是中国社会本身从根基上所发生的变化已经向知识精英发出强烈的呼吁,要求他们为新的生活方式建立长久的规范、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是否对这种呼声作出回应,是当代知识分子应当考虑的问题。
与此相应,第三次启蒙就必须在理论上比前两次有重要的推进,以便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不只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或者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以前启蒙精英的呼吁和老百姓的生活还是两张皮,靠抽象的爱国主义加上亡国灭种的恐惧、振兴中华的理想来鼓动民众的认同,其实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无切实的联系。现在启蒙的原则开始与百姓每天的生活接轨,甚至每个命题都与百姓息息相关。大体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从“科学”深入到“理性”
20世纪的两次启蒙都没有能够深入到西方启蒙的理性精神。在“德先生和赛先生”中,人们关注的“赛先生”是“科学”,但对科学的理解却大都局限于“技术”。五四时期寻求的是“救亡”的政治技术,80年代寻求的是“强国”的科学技术,都是实用的目的,而缺乏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实际上就是理性精神,包括怀疑精神和逻辑精神。
真正的科学精神起源于好奇心,好奇心就是怀疑精神,想要搞清真相,对表面的东西、现成的东西、已知的东西不满足,想要获得未知的东西的知识。实用的目的是满足于知其然,而不必探求其所以然,只要能够获得满意的效果就行了。而理性精神则要求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寻求原理和公理的体系,不仅这一次适用,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它由怀疑精神开路,而由逻辑精神作为指南针,它是远远超出于具体实用目的之上的。
人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而赢得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但我们通常把它理解为“技术”,只有按照这种技术,才能“救中国”。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当代历史的“天道”“天理”,不可抗拒的“铁的规律”。科学当然有规律,但科学更重要的是发现规律和创建规律,人为自然立法。这是中国传统的天理天道所没有的。通常讲的“命运”、“天命”,天经地义,只有服从,没有道理可讲。真正的科学精神不是仅仅服从规律、遵守规律,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建立规律。单纯服从科学规律已不是科学精神,而只是技术,而这种技术与巫术和迷信并没有本质区别。技术就是不问所以然,而按照既定的规则办事,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就会失败,“碰得头破血流”。而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规律,真正的科学精神勿宁说体现在怀疑和“证伪”中。科学家就是要突破现有规律的局限性,而发现更高的规律,这就需要怀疑精神和实验精神,即批判精神。
这样理解的科学就不是人性的束缚、自由的枷锁,而是自由本身。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说它提出了一系列“铁的规律”让人们去遵守和操作,而是由于它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它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一次大胆的尝试和突破。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工具,它更是人性自由的张扬和人生的探索精神。很多人认为,根据目前的“国情”制定一些可操作的政策就是所谓“科学发展观”,其实这只是技术发展观。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没有多少是真正符合科学理性的,只是技术上“只摸石头不过河”的临时应付手段。理性精神的作用就在于根据国情来突破国情、改变国情,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2、从“民主”深入到“人权”
五四以来对民主的理解也有根本性的偏颇,这就是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自上而下的给人民以发表意见的机会(让人说话),或广泛地征求和采纳群众意见。但其中最重要的缺失就是“人权”的缺位。西方民主是建立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个前提,谈何民主?民主不单单是“让人说话”,而是按照天赋人权来制定说话的规则和法制。否则我今天让你说话,明天就可以禁止你说话,甚至把让你说话作为“引蛇出洞”的“阳谋”。民主只有一群自主之民才能建立得起来,而自主之民首先就要对自己的权利有清楚的意识,不是靠别人给了自己什么“权利”就感激涕零,而是自行追求自己应得的合法权利。自主之民意识到,自己的领袖理应为自己“谋幸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选他,或者罢免他,所以人民的领袖不可能成为人民的“大救星”,而是人民的公仆。
民主不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罗伯斯庇尔和列宁搞出来的,是把民主当作集中的工具、也就是极权的工具,是在一个绝对权威的集中控制下把民主玩弄于股掌中。这样的“民主”,连土匪、盗墓贼、黑社会都会玩。真正的民主当然也要有技术上的集中决策(例如投完票之后要人来执行),但这只是工具和手段,而非目的。集中的目的只能是贯彻民主的意志。而民主当然也不是终极目的,因为它对于终极目的来说也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就是人权。民主、集中、人权三者的关系应该是:集中是民主的手段,民主又是人权的手段;或者说,民主是集中的目的,人权又是民主的目的。民主集中制的“变戏法”就在于:利用民主本身只是(人权的)手段而把它转化成了集中的手段,也就是用集中这个(相对的)手段偷换了人权这个(绝对的)目的,从而使集中变成了极权。
人权是天赋权利,它的本质就是自由权。自由之所以成为“权”(right,Recht),就是因为它是靠“法”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具有“公正”的道德内容,这就是宪政。没有宪政,那种为所欲为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最终是虚假的自由。因为,为所欲为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弱肉强食必然导致强中更有强中手,最终导致“强者为王”的专制社会。所以,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法权下的自由,即由一切人所承认的公正原则之下的自由,无法无天的自由不是真自由,无宪政的“民主”只能是多数的暴政、甚至少数或个人的暴政。
对人权的强调是解决当前社会冲突的最重要的核心。维稳的前提和根本就是维权。
3、对普世价值的整体把握
凡是谈普世价值的人都会受到这种质疑:你的那套普世价值是从西方拿来的,所以只不过是西方价值而已。这种质疑根本用不着认真对付,因为它缺乏起码的逻辑常识。任何一种普世价值,都总得由某种文化来承载;如果仅仅因为它由西方文化承载就否定它有成为普世价值的资格,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普世价值。这正如那个不吃葡萄、苹果、梨子、香蕉……而要吃抽象的“水果”的病人一样,是吃不到任何真正的水果的。
其实中国文化历来是承认普世价值的,因为很长时间内我们把自己的价值看作就是“天下”的普世价值;只不过近现代以来我们那一套普世价值暴露出了它的狭隘性,它只是立足于家庭宗法和亲情的“推恩”之上的,推到哪一步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儒家鼓励“亲亲相隐”就是这种狭隘性的典型体现。可见普世价值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提高自身的过程。西方今天的普世价值比中国传统价值更加普世,它可以包括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如“民胞物与”、“仁者爱人”、“孝”等等。因为它的基础建立在更加根本、更加普遍的原则,即人人平等具有的人格、人权原则和理性原则之上。
三、第三次启蒙的任务
1、以“理性”对抗“天理”
首先就是要以真正的理性精神对抗中国传统的“天理”。中国传统的天理在今天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天理是一种规则,但又不可规定、不可言说,只能靠每个人内心去体会,去悟。天理是非理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传授,天理实际上就是“人情”,“人情大于王法”。天理是在人们的人情往来中,在待人接物的得意忘言和“妙悟”中,在行为举止的循规蹈矩、入行随规中,在下级对上级的愚忠、上级对下级的照顾,甚至于在行贿受贿的“小意思”中,而开显出来的。历史上,从孔夫子的“亲亲互隐,直在其中”开始,就把潜规则看作天经地义,说假话、拍马屁、歌功颂德、互相包庇都有了理直气壮的理由。三鹿奶粉以小集团利益损害全国人民的健康,在当事人心目中却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事,只是不能拿到集团外去说而已。所以中国的天理和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有必要加以区分。
中国人每当和人辩论时,虽然也标榜“讲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确定你是“站在谁(或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由此还延伸到“你是什么出身?”今天的网络爱国主义流行的则是“你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所有的“理”都要以这一点为前提,因此所有的讲理都成了“诛心之论”,这就叫“态度问题”、“立场问题”,这里所讲的“理”根本不是合乎理性的道理。“造反有理”要看是造谁的反,合谁的理。所以中国人“讲理”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就是要追溯到一个不容怀疑的天理,来迫使对方“转变立场”,站到这个天理一边来说话和表态。只要立场不对,再有道理、再合乎逻辑的推理都是“狡辩”,都是“别有用心”,那就不用和你讲理了,只须“打倒”便是。立场一对头,胡说八道都有人喝采,被称赞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种讲理不是要搞清客观事实,而是要分清敌我,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人不对事。对待“自己人”,即使犯了天大的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对待异己者,则是“立场问题”,其下场无非是群起而攻之,甚至“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文革的这套潜规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根源,当年的中国人只要有一半具备丝毫的理性精神,就不会造成文革的悲剧。
因此,中国当代启蒙的对象首先就是用真正的理性来对抗传统的“天理”,用逻辑理性和自由精神来揭穿“天理”的扼杀人性、“以理杀人”的本质。
2、以“人权”重建“自由”
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是不讲人权的,这从文革期间的“四大自由”可以看出来,都是侵犯人权的。西方近代自由概念则是一个法制概念和人权概念,不是每个人为所欲为,而是“群己权界”,不是一个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或者多数人凌驾于少数人之上,而是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人权本身是自由和平等的统一,不可能只给一部分人自由,不给另一部分人自由。
在今天,没有权利或法权(rights)的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意识。五四以来所理解的自由大都限于“个性解放”,并且与中国传统的狂狷、性情、童心等等混为一谈,是一个重大失误。文革中利用青少年的青春冲动和逆反心理,把个性解放膨胀为“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法无天”。至今人们还在推崇和欣赏这种“个性”,而没有意识到这种个性自由与启蒙精神中的自由精神、与西方讲人权的自由权利是完全格格不入、甚至相反的。应当揭示这一文化错位,以此重建五四以来的自由观。自由不是“自由化”,而是具有崇高的含义,即人的尊严,人格。当今的“维权”不仅仅是维护一些私人财产,而且是维护人格尊严。这就要有法律。
中国传统儒家厌恶法律,提出“息讼”理想,其代价是牺牲个人的人格尊严;而今天人们动不动就打官司,“法庭上见”,正表明一种个人尊严意识的觉醒。但我们至今还没有给这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提供站得住脚的现代法理根据,人们更相信的是“私了”和“调解”。占据人们头脑的仍然是传统对法律的偏见,即认为法律无非是解决利益冲突、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的工具,却没有意识到法律是保护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的工具。
3、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
什么是健全的启蒙心态?以往启蒙者普遍有一种不健全的心态,就是缺乏谦虚和宽容,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并力图将自己的主张付诸权力,让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特别热衷于从政、抓权,甚至玩权术、搞宗派、窝里斗,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一股政治力量,最终导致启蒙的异化。这是鲁迅当年对他们特别反感的一点。而健全的启蒙心态对待自己的理论对手有种宽容,信奉伏尔泰的名言: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你观点的权利。启蒙在今天的主要理论对手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但真正的启蒙者一方面应与对方进行平等的理论辩析和论战,另一方面也不会把这种理论上的对立扩大到宗派对立甚至政治对立。成熟的启蒙意识把传统观点当作一种观点来对待,致力于与这种观点进行理论上的争鸣,但主要是为了搞清理论问题,而不是打派仗,不是要压制这种观点,而是反对这种观点对其他观点的排除和坑灭。所以就连传统文化本身,也只有在这种宽容之下才能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在现代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得到发展和弘扬。但中国儒家文化最要命的不是具体的观点,而是唯我独尊和大一统的权力诉求,这才是启蒙(和其他一切学术观点、包括儒家本身)的真正敌人,是要坚决反对的。当然它作为一种个人操守是可以容许其存在和值得尊敬的。
结语:启蒙的未来前景
鲁迅当年说,最怕的是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今天已不是鲁迅的时代了,历史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梦醒了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启蒙在今天比90年前更具有社会物质基础,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空想和悲鸣,而显出是历史的必然。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每天都在呼唤启蒙原则,我们有不少文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有感于中国当代社会处于现代化难产的阵痛之中,而尝试回到古老传统中去寻求某种灵丹妙药,他们甚至无端地把当前社会的道德问题归咎于启蒙本身。但回归传统绝对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出路”,而只能是一条死路。即使是传统中的优秀的精华,在今天也只有尽快地实现启蒙的初步原则,才有恢复和“弘扬”的基础,正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先例所昭示的。没有这个前提,回归传统只能是败坏我们的传统。
欢迎大家将好的有关商业领域热点、模式、案例等方面原创或转载的文章、资料等推荐过来,与毕友们一起分享。可直接发至毕友征稿邮箱:2733119529@qq.com,或Q:2733119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