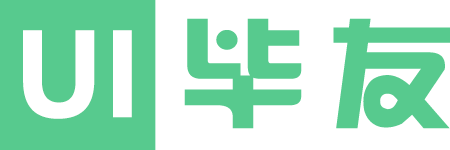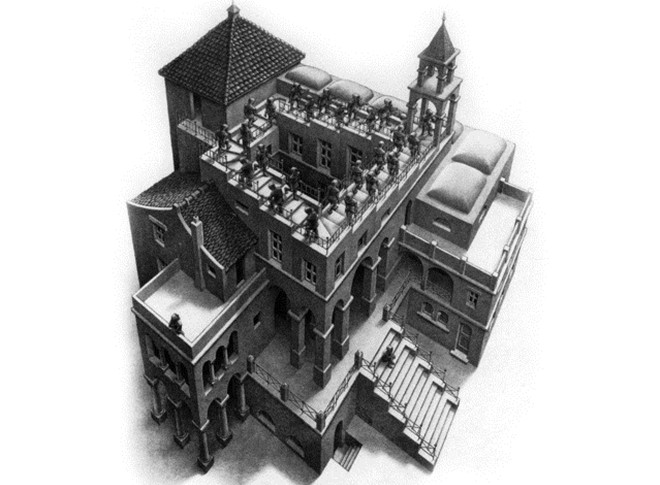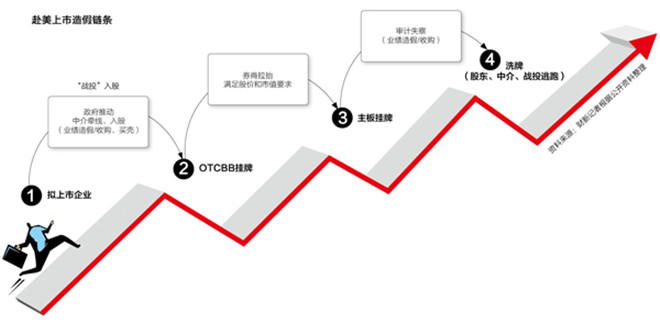(价值中国会联席会长 张晓峰)
推荐语:
“创客”是那伙不安份的一群人——思维开放、玩创新、搞分享、有改造世界的热情,“创活”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乐意称自己是“数字牛仔”,讨厌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创客与其说是一种称谓,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一种生活方式。你我的身上或许都有创客的影子。
当斯坦福的预言学家Paul saffo将美国经济发展历程概括为生产者、消费者、创造者经济时代三个阶段后,人们开始接受这个“创造者社会”,开始观察这个“自媒体”的世界,开始思考创造者经济的规则与创客时代的管理。
创客并非创造者经济时代到来以后才产生。孔子、释迦摩尼、苏格拉底都称得上创客,好莱坞就是创客协作工场。但受全球化、数字化、交互实时化、管理文化变革、知识产权制度等因素驱动,出现克里斯·安德森描绘的“创客运动”则是最近的事情。
Linux的意义决不仅限于鼓励开源软件本身,从App Store到安卓,从博客到微博,从众包到众筹(Crowdfunding),从微信到Kindle,从可汗学院到TED,从C2B到O2O,都不难发现它的影响。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自媒体”取代大众媒体成为主流的传播平台;价值中国、腾讯云中智库、猪八戒网、创新工场等,则是创客的生态化生存平台。
斯隆的Hippel提出“创新的民主化”,指出我们忽略了一种重要的资源——消费者创新的热情和能力。管理世界的变革也让我们看到了曙光:IBM每年都举办打破边界的“创新周”,获得创新启发;宜家通过举办“天才设计”大赛,吸引顾客参加多媒体家居方案的设计;宝马、奥迪也开设了客户创新实验室。
一个人本质上隶属于什么组织,就看他在哪里自愿花费更多的时间或者是“优质时间”。“自愿”不是企业组织完全能够雇佣的。这是企业管理最大的挑战!
管理越来越需要前瞻性、包容性,并做到各得其所。

创客们的黄金时代
文/胡泳
今天,最成功的管理故事都不是公司的胜利,而是对公司的颠覆的胜利。
2012年7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制造业的未来在美国而不在中国》的文章,作者杜克大学企业家精神与商业化研究中心主任Vivek Wadhwa预言:“技术进步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像过去20年里美国制造业那样迅速衰落。”他认为,未来将出现一种“创造者经济”,届时大规模生产将被个性化生产所取代。
无独有偶,《连线》杂志主编、“长尾定律”的提出者克里斯·安德森出版了新作《创客:新工业革命》,在书中讨论“创客文化”,他认为最新的数字科技与古典的“自己动手”的匠艺迎面相遇,构成了一场“新工业革命”。18世纪掀起的工业革命现在进入了它的第三波。
安德森决心身体力行。11月初,他宣布将在年底前离开《连线》,担任3D Robotic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3D Robotics的主要业务是用3D打印技术制造硬件产品。一改软件业长期执IT业之牛耳的状况,现在有人提出“硬件复兴”,原因是开源硬件和3D打印机将制造业带入个人制造阶段。当产品设计和原型生产加速,会建立一个关于制造品的“长尾”市场。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章讲到的分工,200年过去了,美国管理界现在提出了合工理论。企业正在走向分散型加合作型的存在形态。此种形态必然对过去20世纪的管理学遗产带来冲击,我们所知的管理学大概已经走到了尽头。
企业领导人把自己视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然而他们所管理的企业却是为了绕开市场而创生的。企业的出现,是为了回答这样一种挑战:组织成千上万的身处不同地方、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完成巨大而复杂的任务,比如制造汽车或是提供大范围的电话服务。它在工业革命时期曾经有辉煌的战绩,然而200年之后,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员工和分配资源的方式。
今天,最成功的管理故事都不是公司的胜利,而是对公司的颠覆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韦尔奇可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公司创建者。但即使韦尔奇本人,也以向科层体制发起挑战著称。其他的管理明星们都是因为攻击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破坏企业结构、用革命性的策略令大象跳舞而获得声名。换句话说,最好的企业领袖变成了企业的敌人。
理由非常明显。企业是官僚制的一种,而经理本身是官僚。官僚的基本倾向是自我永续,所以,从定义上来看,官僚就会抵御变革。他们的任务不是加强市场力量,而是试图取代、甚至抵制市场力量。甚至是最好的公司,也无法保护自己免于破坏性的旋风般的变化和企业的惯性之间的冲突。正如张瑞敏所指出的,日本企业的衰落不是由于“坏”的管理,而是因为它们遵循“好”的管理的教条。它们认真倾听它们的客户,它们仔细研究市场趋势,它们为可能带来最大回报的创新分配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们却失去了开创新的客户与市场的破坏性创新机会。
由经理人控制的企业无法应付加速地变化,这个弱点只是企业受到的两翼夹攻的一翼。另外一翼是,企业存在的核心理由现在也不保。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他1937年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中论证,“创建企业成为有利可图之事物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存在着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也就是交易费用。对于任何给定的任务,于合适的时间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人来完成,成本太高,也过于复杂;同样,在公开的市场上,寻找供应商、协商价格、规制绩效、保护商业秘密等等,也完全不可行。企业可能也未见得就比市场更善于调配劳动力和资本,然而,它却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也就弥补了市场的弱点。
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互联网时代的曙光刚刚初现。从那时以来,居住在不同的大洲、拥有不同的技巧和兴趣的人们共同工作、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产生了量子跃迁。极其庞杂的事业,如编写维基百科和合成Linux操作系统,在毋需或只需很少管理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的成就,使得像唐·塔普斯科特这样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预测说,“大规模协作”现在成为了经济组织的新形式。他相信,企业的科层制会彻底消失,个体现在被赋权,得以共同创造“一个新纪元,甚至是一个黄金时代,可以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或是雅典民主制的兴起相媲美”。
这当然非常夸张,最不切实际的技术爱好者也很难想象,比如说,一架波音787客机会经由“大规模协作”而建成。然而,趋势的确已然形成,无可否认,交易成本正在快速降低。我们现在既有需求、也有机会设计一种崭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以及一种新的管理科学,以处理21世纪的变化惊人的现实。这一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将更像市场,而不像过去的企业。
节选自《创造者经济与传统管理学的终结》
价值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