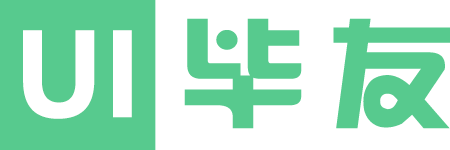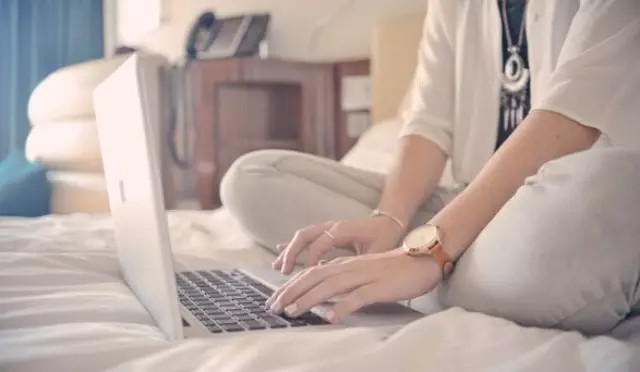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会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这和你的憧憬无关,就像你是一棵苹果树,你憧憬结橘子,但是你还是诚实地结出苹果一样。
女人嫁给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一大不幸,有如诗变成了政治,而字变成了章程。
命运不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走到哪里你都在命中。
人生不能有目的
因为目的是空的
人生不能没目的
因为人生是空的

我发现城市里的人都在说话,说的话跟那些鸟和猪的都不一样。他们有条有理地说。这对于我真正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一直到前不久,我还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和我的妻子去办去美国的签证,那个官员问,你的皮肤是黄色的?是红色的?是黑色的?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我妻子说,好像跟木头的差不多。她问我应该填什么颜色,我说:你可以写“美丽的”。这就是我的愚蠢之处,我没办法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我坐在一棵伐倒的树上,摸着那个新鲜的树桩,有一种白色的光明,一个声音,在我心中醒来,好像穿过一个白色的池塘,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候我看见了我的生活,非常可怜,作为一个男孩儿到男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为了活下去,为了恐惧死亡,我做了这么可怜的事情——我要学习一种语言。

无论怎么分呢,把人分成男人或者女人,分成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分成诗人或者非诗人,我觉得都是一个让一般人心安理得,就是认为自己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好像你一掌握了这个概念,就知道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像我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昆虫是一类的,有的时候跟人是一类的,不是固定的吧。孙悟空吧,我们知道有七十二变嘛,是吧,我也是属猴的,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很难说。那个不是有个“存在主义”吗?我觉得存在主义最好的地方呢,就是这点:你是什么,这个事儿很难说。但是呢,是不是当人呢,这个要看情况而定。
一个人取得食物的能力,同生命的真意有什么关系?能力不过是一种体面的盗窃行径。即使盗窃可能到达真意,体面也不能。世界称颂了贼。
在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等待,一个兔子会来,一个声音会来,甚至神明。
艺术是花的时候,结出神的果,这时哲学是叶子。
从叶到花,或从花到叶,于科研是一个过程,而于生命自身则永远只在此刻。花和叶都是一种记忆方式。果子同时也是种子。生命是闪耀的此刻,不是过程,就像芳香不需要道路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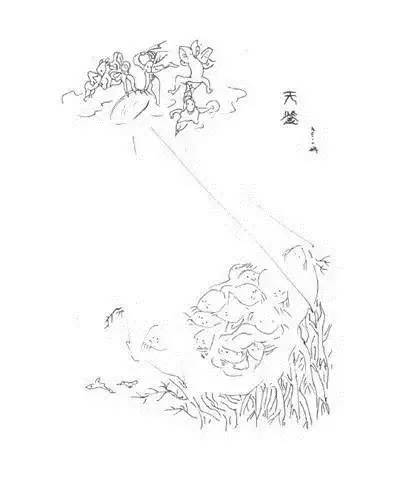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我知道,它一定是简单的,要不人早知道它了。
人以为上树必须有梯子,他们忘了苹果并不是爬上去的。
我信神但不信神要我信它
神那么稀罕人信就不神了有那么可怜的神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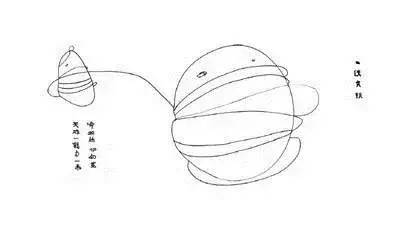
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再简单不过了。人世所以闹得这么复杂,盖是因为加进了目的,一加进这个怪物,立即就复杂无比。你想当博士,就必须啃书本、钻逻辑,甚至琢磨着巴结导师,导师有什么怪癖?有没有孩子?就复杂极了。如果你想当博士,还偏说并不想,而是为了真理,编出另个目的诓世,那就复杂加复杂,不仅复杂了自己,还复杂了有目的的别人,让人们更有根据说世界复杂。
大家都抱怨复杂,却不愿想自己就是复杂的根源,麻烦都是自找的,只要诚心,就会看见世界简单至极。你须做的只是扔掉目的而已。这时你自由自在,人人自由自在,天下太平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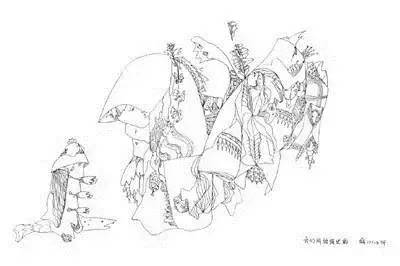
人的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使你不安宁,说它是欲望也行,幻想也行,妄想也行,总之它不可能停下来,它需要一个表达形式。这个形式可能是个革命,也可能是个爱情,可能是搬块石头,也可能是写一首诗。只要这个形式和生命中间的这个能量吻合了,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过程。
中国古代有许多故事讲的其实是行为艺术,比如庖丁解牛、嵇康打铁、阮籍的青白眼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现代艺术已经又一次验证了古代艺术家的方式,艺术似乎不再是某个固有形式的概念了,而扩展为对整个生命真切表达的呼唤过程。
所有被风吹过的树
都显得有神

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光,是一种洁净的感觉,是一种洁净的心境。鬼对于我来说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化身、一个旅行。人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名称,也是一种概念。昆虫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没有妄想的生命。它不会变得很大。世界说我是人就是说我具备了人的形体,但这个形体并不是全部的我。我还能感觉到其他的生活。如果只遵循一种方式生活是非常单调的。光做人也非常单调,不合我的心性。
两个雨滴降落到大地上,微微接近,接近时变长,在临近汇合的最新鲜的刹那,它想起它们分离的一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都作为云、飞鸟、河水,千百次生活过;都作为阳光生活过。当你有了眼睛,看世界,闻到春天的气息,听,声音一闪,你就想起了以前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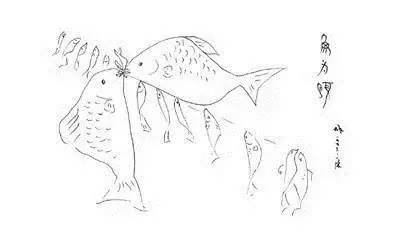
对于美和希望,终究会离开我们,我一直存有大的困惑,这折磨了我可以说很多年——就是浮士德所面临的,他说真美啊,你留下来吧!这时一切就消失了。
这的确是一个折磨人的问题:爱情过去,我们剩下了婚姻;革命过去,我们剩下了政治;诗过去了之后,我们剩下的是诗坛……一个精神的创造力过去了的时候,剩下的可以说是一具尸骸。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不反对什么,也不顺从什么。
只有诚实,很简单。
“没有目的”才能“在蓝天中荡漾”,“没有目的”才能感到心、生命的真切。
我爱他们的时候,我就是他们。

自由并不是你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也不是你干什么都可以不坐牢了;自由是你清楚无疑你要干什么,不装蒜,不矫揉造作,无论什么功利结果,会不会坐牢或者送死,都不在话下了。
对于惶然不知道干什么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存在的;对于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人,自由是不可及的。
“从心所欲不逾矩”——一点儿勉强也没有,任何外力都是无;而“矩”是什么?就是“灵”的“自为”。你超出这个“自为”,加入了非灵的杂念,就是“逾矩”。所以说“从心所欲”和“不逾矩”又是一个东西,只不过“通俗”起见,从相对方向做了强调。
当世界上布满了人,结成了社会,我们不得不承认,需要有统一的规则来使这个社会运转、延续。这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
但这是生存的问题。它不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讲的人的自然属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
自然个体本身是各个不同的,就像庄子说的,有的鸟腿长有的鸟腿短一样,你把长的截短或者把短的接长,这对于它们的自然都是破坏。
而社会要求的是统一,做的正是这件事;又不得不做,否则它无法存在和延续。所以从人的立场来讲便是有得有失。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一直处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状态中——你要求自由,可能就要同时接受死亡;而你接受生活,又往往必须扭曲本性。
不过在中国的哲学里,后来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完全调和了这两者的矛盾——
就是说人大可继续过他的生活,而他的心呢,是自然的;就像云在天上,水在瓶子里一样,彼此一点儿也不矛盾;各在各的领域里,互不相干,安全地并存。
这呢,也算是我的一个座右铭吧——人可以像蚂蚁一样地生活,但是可以像神一样美丽——生如蚁而美如神。
照毛泽东的说法,有生之物,出生之时都是真老虎,后来就变成一个纸的老虎了。如果仅从审美角度讲,那无论如何我更喜欢前期的孙悟空。我实在同意弗洛斯特说的那句话,就是革命只该进行一半,就是前半部分是有意思、有活力的;随后功利、政治跟过来,精神的光芒大大减弱,最初的生气就失去了。
顾城是当代中国文学收获的少数几个天才之一。1987年5月之后,顾城后期思想,多见于谈话、访谈、演讲中,它们的呈现方式带有一定的即兴和片段色彩,这些二十年前的思考对于今天为凡俗生活所困的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灵光闪现有助于我们树立平静生活的智慧。